自英國畫家查普曼在19世紀70年代提出“后現代”概念以來,西方相繼地出現了多次有關傳統、現代、后現代以及“現代性”的爭論,而自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以降,西方理論界掀起了一股強烈的有關“現代性”的話語爭論和理論對話,“現代性”、“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等等語詞成了學者、理論家、藝術家們口語中、文字中的最為常見的理論術語,“的終結”、“的終結”、“文化的終結”、“藝術的終結”等等成了“大眾化”理論家們的口頭禪。更有甚者,解構主義的大師們德里達等人提出了與傳統決裂的超級的現代性口號,開始實踐其現代性藝術的行為悖論。

針對藝術終結論及藝術轉型后的藝術現實,筆者斗膽在已有汗牛充棟的著作問世的理論界再做一些簡單的梳理,謹當是添磚加瓦。關于“藝術終結論”最早始于黑格爾。1817年,黑格爾在海德堡開始了后來被譽為“西方歷史上關于藝術本質的最全面的沉思”的美學演講。

在這次演講中黑格爾提出了一個令西方思想界目瞪口呆振聾發聵的觀點:藝術已經走向終結。在此,暫且撇開黑格爾關于“藝術終結論”的本質闡述,而做“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式的追問,尋找黑格爾的“藝術終結論”的邏輯依據。據《美學》中所描述,黑格爾曾就藝術指出:“就它的最高的職能來說,藝術對于我們現代人已是過去了的事。

因此,它也喪失了真正的真實和生命,已不復能維持它從前在現實中的必需和崇高地位。”那么,是否藝術真的對于“現代人”來說已不復存在或已經消亡了?反之,其“終結論”的內涵及外延又是什么?問題的關鍵恰好在此,這一命題的提出,理所當然大大地刺激了西方后來思想家們的靈感并被迫面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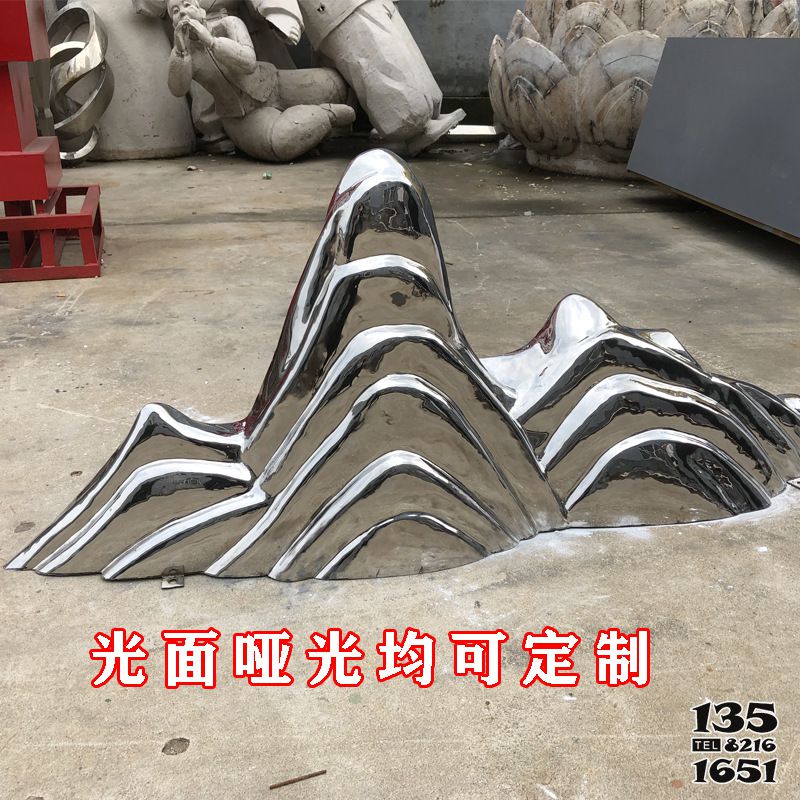
因此,理解“藝術終結論”,清理一下黑格爾關于“藝術終結論”的理論前提是有必要的。黑格爾在演講中指出了藝術的歷史的三種類型并闡述了其中最基本的特征。與各個不同的歷史藝術的內容與形式的相互關系相識應,黑格爾把世界藝術發展的類型分為三種:象征型藝術——古典型藝術——浪漫型藝術。黑格爾把“象征型藝術”稱之為藝術的開端,“是藝術前的藝術”。象征型藝術的主要特征是,物質的表現形式壓倒精神的內容,“理念還在摸索它的正確的藝術表達方式,因為理念本身還是抽象的…

還不能由它本身產生出一種合適的表現方式。”形式和內容的關系僅是一種象征關系,物質不是作為內容的形式來表現內容,而是用某種符號、事物來象征一種朦朧的認識或意蘊。黑格爾認為埃及、印度等東方民族的建筑最具有象征色彩,“它們是些龐大的結晶體,其中隱含一種內在的東西,它們用一種由藝術創造出的外在形象把這種內在的東西包圍起來…標志這樣一種內在精神的形象對于它所確立的內容還只是一種外在形式和外圍。
金字塔就是這樣一種隱藏內在精神的外圍。”但是,隨著歷史的發展,人類心智的不斷成長,其藝術創造的內在的東西不愿受巨大的物質形式的束縛而逐步從自在走向自覺。藝術創造中的內容和形式的巨大反差,開始向新的方向轉化,因之,古典型藝術便應這種發展的趨勢產生了。“古典型藝術”在黑格爾目中是最完美的藝術,是內容與形式、精神與質料的最完美的結合與和諧。
他說:“古典型藝術是理想的符合本質的表現,是美的國度達到金甌無缺的情況。沒有什么比它更美,現在沒有,將來也不會有。”“內容和完全適應內容的形式達到獨立完整統一,因而形成一種自由的整體,這就是藝術的中心。”黑格爾把古典型藝術的理想典范歸之為古希臘藝術,而最符合這種理念美的藝術是雕刻。這種藝術形式一方面理想性較強,適宜表現神們的靜穆和悅的特點——溫克爾曼曾就古希臘藝術提出著名的“高貴的單純和靜穆的偉大”的觀點。
而另一方面又把神們的性格化為完全具有人類的面貌,并付諸達到完備程度。黑格爾曾一度強調這種“理想性格模型”。但是,創作的發展并不會永遠停留在這樣一種形式之中,即使是“最完美的藝術”也不例外。根據黑格爾本人的觀點:理念是發展變化的,它的運動牽引力必然在發展中不斷壯大,最終打破古典型藝術和諧的狀態,而沖出這種狀態,并逐漸超越并控制創作形式成為主體。
誠同黑格爾所說:“精神愈感覺到它的外在現實的形象配不上它,它就愈不能從這種外在形象中找到滿足,愈不能通過自己與這種形象的統一去達到自己與自己的和解。”“浪漫型藝術”就在這種發展趨勢中取代了“古典型藝術”。主體性原則是浪漫型藝術的基本原則,絕對精神不斷克服外在形式的阻礙而回復到自身的本性,這種主體原則的真正內容是絕對的內心生活,即一種情感沖動,人之性格獨立占主導地位。
黑格爾說“浪漫型藝術的原則在于不斷擴大的普遍性和經常活動在心靈深處的東西,它的基調是的,而結合到一定的觀念內容時是抒情的,抒情仿佛是浪漫型藝術的基本特征,它的這種調質也到史詩和戲劇,甚至于像一陣心靈吹來的氣息,也圍繞著造型藝術作品蕩漾著,因為在造型藝術作品里,精神和心靈要通過其中每一形象向精神和心靈說話。
”其典型代表是中世紀的基督教藝術以及近代的小說、繪畫、戲劇等。誠然,精神內容超出物質形式,進一步的發展必然造成作為主體的精神的超越和作為客體的物質形式之間的決裂。依黑格爾看,這種分裂不但導致浪漫藝術的解體,而且也要導致藝術本身的解體。“因此浪漫型藝術就到了它發展的終點,外在方面和內在方面一般都變成了偶然的,而這兩方面也是彼此割裂的。由于這種情況,藝術就否定了它自己,就顯出意識有必要找比藝術更高的形式去掌握真實。
”黑格爾認為這種讓位或轉化的位置理應由宗教或哲學——尤其是哲學——來代替。終于,世界藝術的“終結”在此發展的鏈條上完成了。問題中的問題是藝術終結后的藝術將何去何從,是終結還是轉型?而轉型后的藝術又“何以可能”?從上面的論述可以看出,黑格爾的“藝術終結論”并非提出藝術的消亡,藝術不再存在,而實質上談論的是藝術創作中的神圣性的救贖和啟蒙功能,在浪漫型藝術之后已被猥褻或轉化成另一類型的藝術。法蘭克福學派的著名哲學家阿多諾就曾確認這種藝術演化的事實,并且肯定了“黑格爾關于藝術可能衰亡的展望是合乎藝術的已成狀態的”,而這種觀點在現代確實得到了證明。
在黑格爾看來,藝術的中心就是理想的獨立自足的人物性格,現代技術現實中的每個人都被“一般常規的機械方式”的生活支配著,人變得那么渺小、孤獨、不自由,怎么能夠企望藝術中出現有勇氣和力量掌握現實的充實的性格呢?——這種性格已被“散文氣味的現代情況”所淹沒。因此,藝術創作作為“最高的真理樣式”在現在或未來中終結了。那么,藝術終結后的藝術是以何種面目再現呢?它的主體意義又是什么呢?
對此,黑格爾并沒有給我們完整的答案,也沒有指明后世藝術發展的方向。而不管藝術是否誠如黑格爾意義上的已經“終結”,也不管“終結”后的新藝術形式、內容等是否有意義、是否為現代人所接受,事實是藝術“轉型”確已存在,而且來勢并非弱小,甚至沖擊并動搖了整個現代藝術的審美之維。
現代藝術的流派之多,創作花樣之雜,表現形式之眩目,內容之怪誕前所未有。在此暫且按下不表。且看在布雷德伯編著的《現代主義》一書中是如何描述的:被現代人認為是現代藝術經典的現代主義藝術使得藝術的內容、意義和藝術形式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它并不是暗示倒轉、甚至倒退的變革,而是解體,是退化、有些人說是崩潰。
它的特征是災難性的”,“至于今天以后現代主義自命的藝術,干脆以消解歷史意識,消平深度模式,拒斥主體意識等等而自鳴得意:這一切看來都雄辯地表明,藝術之形雖然存在,但藝術之神已然遠游。”豐書在《后現代藝術的悖論》一文中指出:“后現代藝術是一種沒有統一目標的散亂現象,從中只能理出兩種對立的極端傾向:一是完全拋棄對象,運用語詞、身份語言和戲劇化表演技巧表現觀念;
二是轉向巨大無比的實體物象。”如大地藝術和環境藝術就屬此類。阿多諾也批評了這種現代“精神”。他指出:“在資本主義商品交換中,全社會都在交換中硬結成一種交換的金錢尺度,藝術生產變成了純粹的商品生產。藝術成了一種商品交換而非滿足人的精神需要,藝術創作中作家的靈感和活生生的生命被商品這鐵腕所扼殺。”阿多諾接著在論及現代藝術的命運時,指出現代藝術生存的兩種危機。
一種是“意義的危機”;一種是“顯現的危機”。“意義的危機”是指藝術作品在——“現實的沒落”——歷史喪失意義的前提下難以與自身協合為意義聯系,并且以抗拒意義聯系的觀念對此做出回答。阿多諾指出,現代西方藝術在藝術形式、藝術結構、藝術風格等方面都“給人以刺眼的印象,給人以一種奇特的感覺,既難以理解又難以鑒賞。
一切關于藝術的意義和傳統理論范疇都和現代藝術格格不入,與現代藝術陷入了沖突,在現代藝術面前失敗了。”藝術的真理內容、藝術的表現形式都陷入了重重危機。“被認為構成了藝術作品本質性統一的美和善成為一個不可能的對立面的統一,因為真與美日益成為不可比的。”馬爾庫塞也批評了構成現代藝術主流之一的“大眾化”藝術,指出大眾化流行藝術腐蝕心靈,使“人們變成了整個文化機器中的小零件,在卑微的感官享樂中,以一種所謂的‘幸福意識’取代了‘不幸意識’,即沉淪和屈從取代了覺醒和反抗,最終掩蓋了人的異化這一真相,重新阻絕了人們對現實懷疑的反思之多路。
”而頗具戲劇色彩的是,顛覆傳統,“重估一切價值”的尼采卻仍維護著藝術的“尊嚴”,仍把藝術當作“形而上學的生命活動”,“唯有藝術才能拯救人生”。在《權力意志》中,尼采指出:“藝術無非就是藝術,它乃使生命成為可能的壯舉,是生命的誘惑者,是生命的偉大的興奮劑。”尼采還指出了“現代文化的根本弊病是用虛假的繁榮和人為的亢奮掩蓋內在的貧乏和枯竭。”這種現代性已經破除了“藝術與一般人工產品的界限,不僅將日常生活的材料視為題材,有時干脆將之變成藝術作品。
藝術與非藝術的世界顯現了一種不穩定關系”,“高雅和低俗文化在此化為一體,其融合的目的不是要調和其對立的因素,而是強化它們之間令人啼笑皆非的游戲感。”這種現代性行為已經將藝術作為人類精神的最高旨趣全面顛覆。
而現代派藝術家們普遍認為,現實世界是荒誕的,世界是沒有意義的,沒有意義的世界是非理性的,因此,藝術世界也是非理性的,它無須按照理性的旨意去安排藝術生活。藝術是線和色彩的組合,線和色彩是隨意的,所以,藝術也是隨意的、非理性的。達芬奇的“繪畫是一門”的論斷在現代藝術面前變得多么幼稚。培根在臨終前抱怨說:“一切藝術現都成了十足的游戲,人貶低了自己。
人們也許說,情況歷來就如此,但日前,藝術完全是一種游戲。令人迷惑的是,對藝術家來說,藝術變得更難了,因為他要想成為好畫家,就必須不斷玩出新花招。”可見,“對于現代藝術來說,任何一個流派,無論當年如何先鋒,如何前衛,但變成了傳統,就只能黯然傷神地退出歷史的舞臺,讓位于后來人。”這是現代藝術的特征之一:大起大落,瞬間即逝。
現代藝術放棄嚴肅性而趨向非理性主義、相對主義和虛無主義,放棄了藝術所設定的“理性的統一主體,轉向社會、文化和語言的‘非中心化’了的破裂主體”,使得現代藝術創作的主體性的無限膨脹和工具理性的極度張揚造成了藝術創作中對價值關懷和意義追求都逐漸弱化甚至喪失,并使作品個體價值日趨商品化,這種創作的結果是相當危險的。
我們可以透過現代藝術創作的流程看到現代藝術的躁動不安,拼命追求藝術新形式。諸如達達主義的符號形式,波普風格的圖像拼貼,立體主義的形體相疊,蒙克形式的線條扭曲,野獸畫派的平面構圖,等等,無不以怪誕抽象的畫面出現,無不以不承認永恒,反權威,打破偶像等作為其“價值”追求,表現出一種極端的現代性行為,并企圖用自我的精英理性去沖毀傳統基積下來的文化積淀和審美心理結構,力圖把握自由生命之脈,重新構建起一種屬于自我意識下的話語創作空間。
從某種意義上說,“人們不再懷念整體和統一,不再追求本質與真理,不再尋求概念與感知的一致,這是一個因其模糊而無法表達的屬于內在感受的時代”。海德格爾非常憂慮這個以“體驗”和“感受”作為“藝術欣賞甚至藝術創作的標準”的時代,“到處是光怪陸離的景色,一個消失,另一個立即代之而起”,因為這是個“致藝術于死地”的技術手段,它以雙重性迷惑著體驗者,使他們“深信著瞬間的體驗直面著存在的永恒”而志滿意得。
就連杜威這個實用主義哲學家也批判了這種機械化所導致的藝術異化,其結果是產生一種特殊的審美上的“個體主義”,以“自我表現”來與外界拉開距離,企圖為藝術蒙上一種玄妙的色彩。廣告“做女人挺好”無疑也是現代藝術追求“自我表現”,追求主客體內在體驗和審美感受的一種象征和極端的現代性行為。在此意義上,現代藝術擯棄傳統藝術對藝術的追問和價值關懷而走向表現形式的極端使得人們的審美視界逐漸模糊——審美對象的、審美自身的。就其價值關懷和意義追求來說,現代藝術是普遍缺席的。
藝術之為藝術不僅僅是對個性的極端張揚和形式上的標新立異,企圖嘩眾取寵,“藝術本質上是某種超越了個人,象征和代表著人類共同命運永恒的東西。”它“作為一束神圣的光源的投射”,它必須對人類心智的成長提供更多的精神營養,尤其是神圣的美的體驗以及睿智的知解力。與黑格爾同時代的德國哲學家謝林說:“沒有審美感,人根本無法成為一個富有精神的人,也根本無權充滿人的精神去談論歷史。
”而“藝術終結”后的現代藝術更多是建立在目的性、商品化與技術因素上的,現代技術的“超前”使得“技術復制”在大工業生產中被廣泛,“眾多摹本代替了獨一無二的藝術精品,技術復制終于使真品和摹本的區分喪失了意義,本真性的批判標準開始坍塌。”此外,“現代藝術成為時代的主流,不僅僅是藝術本身發展的結果,正如某些論者指出的,是藝術家諸如唯美主義者追求藝術自律走上的極端。
”“就藝術的起源來看,藝術無疑是一種集體的歌吟,是大寫的人的詩史,其實質是超個性的,”而現代藝術卻擯棄了這種共性而明顯個性化,最明顯的特征就是藝術的分化,作為主體的藝術家的和作為客體的大眾化藝術找不到合適的對話位置:前者因個性的張揚和自律日益邊緣化,后者卻以“機械復制”出大量產品;前者是可能性對話和弱化,后者是游戲本真性的喪失,這是對早期藝術的充滿性和自明性的分裂。
這樣,現代主義藝術在它的意義和顯現方面向自己進攻,使自己成為不可讀的,不再美的藝術,也強迫自己從大眾人群和精神生活中退場,“從而使自己成為話語場上無根的幽靈”。王建疆曾指出:藝術“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處于尷尬的境地。傳統的形而上學的美的探討由于無法與現實的審美實踐勾通而被束之高閣了,而現代以審美經驗為對象的形而上學的美學也在現代藝術的光怪陸離之中失去了建構自己的支點,在一派眩惑之中迷失了自身。
”“所以,藝術的使命就在于替一個民族的精神找到合適的藝術表現”,這樣,藝術才有永久的魅力。當代人是無法拋棄精英意識去和傳統進行精神對話的,這種生活的商業化目的與后的技術理性,使其必受一種淺薄的享受和感性愉悅的通俗藝術所蒙騙,甚至曾風靡一時的后藝術也無法在傳統的神圣意義與現代的大眾化中走出,而使自己處于兩難境地。而整個現代藝術以追求一種非整體的、抽象的怪誕的支離破碎、或者說是一種碎片的組合和拼貼作為手段,以標新立異的手法來博取大眾的一絲同情,并以自我疏離的精神安慰來保持自我的精英意識。
誠然,現代性的思維方式無疑使藝術創作在其立場上有更廣闊的話語空間和表現形式,但是,相對而言,永恒的東西總是精神的延續,而現代藝術貶斥永恒,追求不確定性,排斥所指,企圖建立能指神話,就其主體——精神——意義來說,使得它在“傳統”面前“失語”了。其實,當代藝術家的邊緣地位與其說是大眾化的狹隘的藝術鑒賞眼界及藝術審美本身的弱化造成的,毋寧說是藝術家本身的高貴的自欺欺人的作法造就自己。到此,“藝術終結論”似乎可以找到它的內在的邏輯依據。
在此意義上,黑格爾的“藝術終結論”終見端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