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對(duì)原始生命力的追求亨利·摩爾常常強(qiáng)調(diào)古墨西哥藝術(shù)對(duì)自己的影響。瑪雅藝術(shù)是一種山地人長(zhǎng)期生活在相當(dāng)艱苦的環(huán)境中形成的,他們使用的材料是比較粗獷的石頭,這就使作品顯得堅(jiān)強(qiáng)、凝重、渾厚、簡(jiǎn)樸,充滿了陽剛之美,甚至帶有一點(diǎn)神秘的獰厲之氣,這是原始生命力的體現(xiàn),而這種氣質(zhì)剛好符合亨利·摩爾自己的性格。當(dāng)然,這時(shí)歐洲的藝術(shù)界對(duì)原始藝術(shù)的愛好和追求已逐漸形成一股強(qiáng)大的潮流,無疑也會(huì)影響年輕的亨利·摩爾。

他當(dāng)時(shí)認(rèn)為,雕刻的力度、石頭材質(zhì)感的充分發(fā)揮,已無過于古墨西哥藝術(shù)了。他于是手模心追,以致早期的雕刻明顯具有古墨西哥雕刻的痕跡。正如約翰·羅森斯坦所說:“摩爾對(duì)墨西哥和其他古代雕刻的刻苦學(xué)習(xí),其結(jié)果與原作相比,不過是練習(xí)。強(qiáng)有力而敏感的,但仍不過是練習(xí)而已。”這種對(duì)古墨西哥藝術(shù)的學(xué)習(xí)熱情是會(huì)隨著時(shí)間的推移而淡化的,但他學(xué)習(xí)的本質(zhì)卻并不限于古墨西哥藝術(shù)的某些形式。他更多的是通過古墨西哥藝術(shù)的表面而直探藝術(shù)的本源,這就是一種強(qiáng)大的原始生命力,對(duì)這種強(qiáng)大生命力的崇敬和探討則貫穿了亨利·摩爾的一生。

他曾說,藝術(shù)有兩種重要品質(zhì):一種是“美”,另一種是“生命力”。對(duì)他來說,“生命力”更為重要。在亨利·摩爾漫長(zhǎng)的一生中,他不斷對(duì)各種形體進(jìn)行探索,而他極富創(chuàng)造性發(fā)現(xiàn)了骨骼之美。他看到,正是骨骼才最能表現(xiàn)出“力度”,表現(xiàn)出“生命力”的本質(zhì)特征,這正是他研究體現(xiàn)生命力的形體的合乎邏輯的結(jié)果。二、表現(xiàn)永恒的人性,人性的尊嚴(yán)、人性的溫暖、人性的偉大和堅(jiān)強(qiáng)對(duì)“生命力”的追求,必然導(dǎo)致對(duì)人類自身的肯定,人類是自然界有機(jī)體發(fā)展的最高體現(xiàn)。摩爾做了種種嘗試和探索,用過立體主義的方法,超現(xiàn)實(shí)主義的方法,以至抽象的方法,他說:“總要表現(xiàn)出人性和人性的溫暖。

”特別是在二戰(zhàn)之中,他畫了“掩蔽一部”系列,又畫了“礦工在工作”系列,他說:“它把我做的一切都人性化了,人道主義化了,我都知道,這時(shí)我畫的速寫體現(xiàn)了我藝術(shù)的轉(zhuǎn)折點(diǎn)。”的確,他的作品自此之后充滿了對(duì)人類的希望和信心。他的追求是表現(xiàn)全人類共有的人性。

永恒長(zhǎng)存,與大地山川相始終。在中國美術(shù)館的展覽會(huì)上,有位觀眾要我比較羅丹和摩爾的成就。我認(rèn)為,羅丹總是捕捉人類的某種激情,往往是巨大的痛苦與歡樂,他把剎那間情感升華了,固定了下來,這當(dāng)然是偉大的。而摩爾追求的卻是一種更為本質(zhì)、更為永恒的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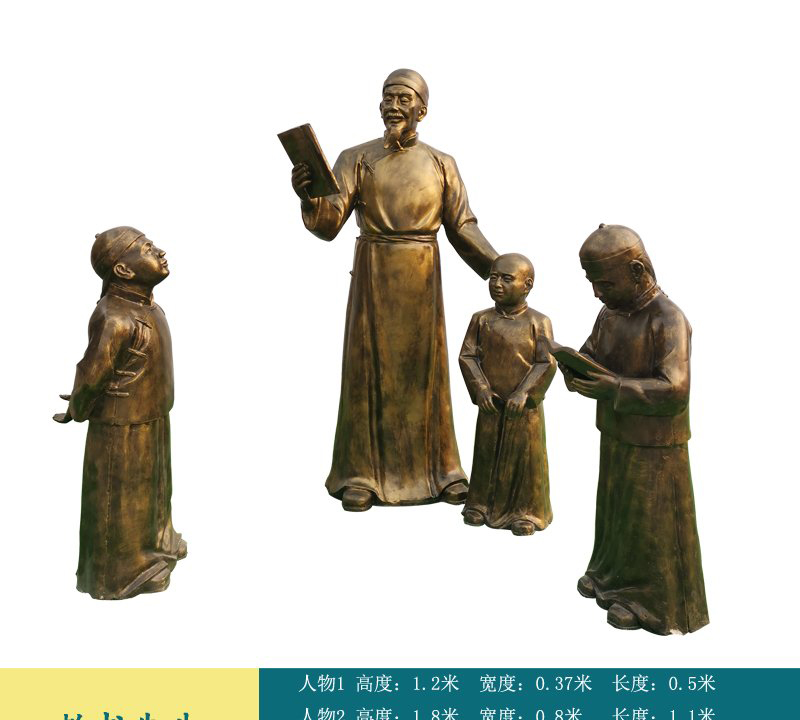
他的作品去掉了民族的界限,去掉了時(shí)代的界限,去掉了地域的界限。他的“人”無始無終,非今非古,不分地域,不論種族,甚至去掉了一時(shí)的悲傷和一時(shí)的歡樂;它是超時(shí)空的永恒的“人”,是全人類的濃縮,是個(gè)大寫的“人”。如此概括而集中,如此出奇而平常,這是前所未有的創(chuàng)造,這是不可重復(fù)、無從代替的杰作。所以,摩爾是偉大的。
十九世紀(jì)的羅丹,二十世紀(jì)的摩爾都是偉大的,而偉大與偉大之間不能相比。他們都是人類藝術(shù)的高峰,都將永遠(yuǎn)為人類所珍視。三、對(duì)雕塑藝術(shù)空間觀念的拓展摩爾十分強(qiáng)調(diào)雕塑家要培養(yǎng)對(duì)空間觀念和空間美感的敏感性。他指出:人們的空間觀念本來就弱于平面觀念。如一個(gè)嬰孩對(duì)事物的大小方圓很快就能辨認(rèn),但對(duì)事物的空間距離卻往往判斷不準(zhǔn);而一般人由于生活所需,漸漸學(xué)會(huì)了正確判斷,但也限于生活所需,只要能應(yīng)付得了,也就不再留心了。
但雕刻家卻要永遠(yuǎn)鍛煉,以發(fā)展這種判斷能力。摩爾在這兒說了正確判斷空間的重要性,要培養(yǎng)一種對(duì)空間的高度敏銳感。事實(shí)上,雕塑家非但要培養(yǎng)一種準(zhǔn)確判斷力,還必須把一般的科學(xué)范圍的判斷變成充滿感情色彩的、對(duì)于空間的美感。如他在中國美術(shù)館中央大廳所展出的坐著的半身女人體。她那胸腹之間的大起大伏,已不是正確關(guān)系的需要,而是空間美感的需要。他要求大出大進(jìn)的空間以表現(xiàn)一種宏偉感。摩爾從空間美感出發(fā),理解到在一個(gè)雕塑實(shí)體上設(shè)計(jì)一個(gè)孔洞,這孔洞將與實(shí)體具有同等的造型價(jià)值,不知是否受了比他早的雕刻家阿基賓可的影響,因?yàn)榘⒒e可創(chuàng)造了一個(gè)乳房凸起、另一個(gè)乳房凹挖的女人體,并說過:這凸形和凹形具有相等的造型價(jià)值。
當(dāng)然,摩爾比他更徹底。摩爾進(jìn)行了一系列雕塑的“內(nèi)部空間”的探索。簡(jiǎn)單說,也就是在實(shí)體中的空間處理。作為一個(gè)中國人,很自然會(huì)想到,他一定受到中國太湖石的影響。后來讀了一些摩爾的著作和談話,才知道他根本沒有提到太湖石,但在這次展覽中卻看到了他收集到不少帶孔洞的石塊,這么看來,他還是受到了不是太湖石的太湖石的影響,是對(duì)自然觀察而得到的啟發(fā)。他說了四點(diǎn)道理:一、一個(gè)經(jīng)過精心設(shè)計(jì)的洞往往可以加強(qiáng)這個(gè)雕塑的三度空間感。
二、雕塑上的孔洞可以加強(qiáng)雕塑和周圍環(huán)境的聯(lián)系,使這個(gè)雕塑更好地融入環(huán)境之中。我體會(huì),中國庭院中的墻上往往挖些方形、圓形、扇面形的洞,它們立即使這面墻和周圍環(huán)境融為一體,墻與環(huán)境有相得益彰之美。三、在實(shí)體中的洞往往比實(shí)體更有力,如墻中有一拱門,更增加了墻的力度。
四、洞往往更吸引人。如山上有一個(gè)洞,則人人都想去看看。這些理論的價(jià)值在于都建立在實(shí)踐的基礎(chǔ)之上,可以在摩爾的作品中找到實(shí)例。與此同時(shí),他又進(jìn)一步研究實(shí)體的外部空間問題,他說“空間是由實(shí)體形成的”,這就不僅指雕塑的內(nèi)部空間了,而是指雕塑的建立也創(chuàng)造了新的外部空間。馬國馨先生說得好,他說,一個(gè)好雕塑同時(shí)也創(chuàng)造了嶄新的外部空間,在雕塑周圍會(huì)形成一個(gè)“場(chǎng)”。摩爾舉了一個(gè)簡(jiǎn)單不過的例子,他舉起食指和姆指,叉開以后就形成一個(gè)三角形空間,這個(gè)三角形空間是因?yàn)橛兄骈_的兩個(gè)手指的實(shí)體。
我們可以引申一下,一片遼闊的風(fēng)景正是由于有近景、中景和遠(yuǎn)景三段實(shí)體的對(duì)比存在,否則什么空間感都無從產(chǎn)生。蘇格蘭有一片荒涼的牧場(chǎng),但當(dāng)摩爾的“帝后像”被牧場(chǎng)主人置放于荒原高處之后,整個(gè)荒原在雕像的視野范圍之內(nèi)完全改變了,使人感到有一種童話般的古老英國的歷史滄桑感。這個(gè)雕塑的確創(chuàng)造了一個(gè)嶄新的空間,創(chuàng)造了一個(gè)富有魅力的“場(chǎng)”。
還有很多如兩件組合臥像第二號(hào)等等,都證明了摩爾所說“空間是由實(shí)體創(chuàng)造的”這一論斷。但按我們中國人的哲理來說,他似乎還少說了另外一句話,那話是“實(shí)體是由空間產(chǎn)生的”。我們先哲早就說過“虛實(shí)相生”,這種理論在中國的篆刻界中成為普遍施行的原則,在中國畫中也早是常識(shí),而雕塑界中卻沒人作過類似的實(shí)踐,更沒有如此系統(tǒng)切實(shí)的理論。四、對(duì)“潛能”與“顯能”的理解與運(yùn)用摩爾把“潛能”的神秘性和實(shí)際調(diào)動(dòng)潛能的方法談得清清楚楚。
我們的觀眾對(duì)摩爾的造型表示不能理解,其根本原因恐怕就在于對(duì)“潛能”創(chuàng)作方法的不理解和不熟悉。所以,要解讀摩爾創(chuàng)作的重要方面,需要對(duì)“潛能”有一些初步的了解。“潛能”也稱“本能”,是19世紀(jì)一位精神分析專家弗洛伊德提出的,是一種深層意識(shí)狀態(tài)。也叫做“下意識(shí)”狀態(tài)。
英國藝術(shù)理論家赫伯特·里德談到亨利·摩爾時(shí)說:“他敢于從下意識(shí)中去探求代表著隱藏在最深處的以及表現(xiàn)的最有力的生命的原始形體。藝術(shù)的現(xiàn)代運(yùn)動(dòng)的特點(diǎn)就在于這一點(diǎn)新的啟示。”摩爾自己說:“我對(duì)我的雕刻的解釋往往是事后產(chǎn)生的,我并不是按個(gè)大綱或企圖表達(dá)某種明確意念才做雕刻的。
在工作中,我常作部分的修改,因?yàn)槲也幌矚g它們那種樣子,我希望它們更好些。這種更改我不經(jīng)思索,憑著直覺去變化。我不向自己提出需要大一點(diǎn)或小一點(diǎn),我只是看著它。如果不喜歡,就將它改動(dòng)。我根據(jù)喜歡不喜歡工作,并不靠什么理性邏輯,也不靠語言,只靠對(duì)形體的愜意與否而定。
過后,我可以作出解釋,或找到創(chuàng)作它的種種理由,但這些卻是‘馬后炮’。但在當(dāng)時(shí)卻根本沒有想過,至少不存在于我當(dāng)時(shí)覺醒的意識(shí)之中。”我想,在這里,摩爾已十分清晰地說明了他憑“下意識(shí)”、憑“潛能”的發(fā)揮而進(jìn)行創(chuàng)作的過程了。現(xiàn)在的問題是我們中國的觀眾,中國的藝術(shù)家怎樣來理解這種方法,這種方法對(duì)我們有哪些啟迪或參考的作用。我自己作為一個(gè)在“社會(huì)主義現(xiàn)實(shí)主義”這個(gè)體系內(nèi)成長(zhǎng)的藝術(shù)家,一開始是完全不能接受這種“不自覺”的創(chuàng)作方法的,覺得真是“豈有此理”,怎么能沒有明確意圖的創(chuàng)作呢?
但一細(xì)想,卻覺得大有道理。其實(shí)在我們自己的實(shí)踐中也經(jīng)常地運(yùn)用這種“說不清楚的”、憑直覺辦事的經(jīng)驗(yàn)。我們自己在修改作品時(shí)或者給同行們提意見時(shí),往往說:“這樣不舒服,那樣好像舒服一點(diǎn)。”要我仔細(xì)解釋,往往也說不清楚,而聽者卻也往往心領(lǐng)神會(huì),而有所改進(jìn)。這舒服與否,我看就接近摩爾的“喜歡不喜歡”了。這種感覺其實(shí)是極復(fù)雜因素的綜合,往往是多方面“文化積淀”的結(jié)果。
它已成為一種“反應(yīng)”,一種“直覺”,已不可能條分理析地說清,但那綜合性的感覺卻往往是十分準(zhǔn)確的。與此同時(shí),我還有一點(diǎn)可以理解這種不自覺創(chuàng)作方法的本錢,因?yàn)槲沂且粋€(gè)書法愛好者。在書法創(chuàng)作中,特別是草書中,這種不自覺方法的采用可就是常事了。誰去打了詳細(xì)稿子去寫字呢?
而且如果真有人打了細(xì)稿再寫,那肯定不是好字,肯定是毫無生氣的了。書法的創(chuàng)作往往是一筆定局,是第一筆決定第二筆,第二筆決定第三筆,落筆之后已自成體系,自定格局,作者只憑一種氣氛,一種愛好,一種情緒,一種勢(shì)頭,一種對(duì)虛實(shí)、輕重、松緊、快慢、枯潤(rùn)、濃淡這些節(jié)奏韻律的高度敏感,信筆直書,一氣呵成。這時(shí)作者所需要的是不受干擾,不受拘束,不受指使和限制。我相信這就是憑“潛能”創(chuàng)作了,就是亨利·摩爾不能預(yù)先訂一大綱來創(chuàng)作的原因了。我想,只要把這種原則,用筆墨憑著對(duì)輕重、濃淡、枯潤(rùn)、快慢的節(jié)奏規(guī)律和美感素養(yǎng),自由地“生發(fā)”開去。
在平面上作書法,換成用石頭、泥巴憑著對(duì)方圓、空實(shí)、軟硬、鈍尖等等的節(jié)奏規(guī)律和美感素養(yǎng)自由地“生發(fā)”開去,在立體空間中創(chuàng)作雕塑,那就十分接近摩爾的創(chuàng)作過程了。只有這樣創(chuàng)作才會(huì)充滿創(chuàng)造的樂趣,才會(huì)產(chǎn)生不可預(yù)料的“生氣”,才會(huì)給作者和觀眾帶來驚喜。我想我以自己的方式領(lǐng)會(huì)了摩爾以“潛能”創(chuàng)作的一個(gè)方面。但亨利·摩爾是英國人,他有一種十分實(shí)在執(zhí)著的脾氣,他決不語焉不詳。
他進(jìn)一步談了他的潛能運(yùn)用的法門。他說:“我想繪畫雕刻的最早開頭從哪一端起始都是可以的,誠如我自己的經(jīng)驗(yàn)所表明的那樣,我有時(shí)并非要去解決預(yù)想的問題就開始畫起來了,只是想在紙上用鉛筆,并無自覺目的地用線條、調(diào)子和形體,但是當(dāng)我的理智接受了這么產(chǎn)生的東西之后,就達(dá)到了這一點(diǎn),即某些觀念變得自覺了,清晰了,于是一種控制和秩序就取而代之了。
”《雕刻家發(fā)言》這兒摩爾進(jìn)一步闡明了,他并非只是憑“潛能”創(chuàng)作,而是把“潛能”和“顯能”不自覺和自覺結(jié)合起來,這才是創(chuàng)作的全過程。他在同一文中接著說:“但是,雖然在他的作品中他心中的非邏輯性、本能性、超意識(shí)性肯定在起作用,而同時(shí),他還具有并非不起作用的自覺的觀念。藝術(shù)家是以自己的全身心來工作的,而他的自覺部分就調(diào)和和解決矛盾,組織回憶和防止他同時(shí)走向兩極。
”他說的太好了,我從來沒有讀到和聽到過如此誠懇、切實(shí)的談“潛能和顯能”如何交互作用的文章。我又要用我所熟悉的中國書法家的理論來解讀摩爾的這段話了。這段話的關(guān)鍵是潛能和顯能的交互作用,但摩爾只說了一個(gè)基本過程,就是先是“潛能”作用后為“顯能”所接受并加以調(diào)整,而我們的懷素自敘中卻說了一段更為詳盡的話。懷素引用了戴敘倫送他的一首詩:“心手相師勢(shì)轉(zhuǎn)奇,詭形怪狀翻合宜。
人人欲問此中妙,懷素自云初不知。”這首詩的關(guān)鍵是指出“心手相師”。心當(dāng)然是“自覺”,是“意識(shí)”,是“顯能”。而“手”就是不經(jīng)過心,不經(jīng)過思考的手的運(yùn)動(dòng),是“不自覺”,是“下意識(shí)”,是“潛能”,而妙就妙在說出了“相師”二字。這樣就補(bǔ)充了亨利·摩爾所提到的單一的從潛能過渡到顯能的過程。這里說了“相師”的過程,是不自覺過渡到自覺,而在創(chuàng)作進(jìn)行中又會(huì)有新的不自覺因素的出現(xiàn)。
于是又為新的自覺因素所接受,所調(diào)整,其實(shí)整個(gè)創(chuàng)作過程是個(gè)不斷由潛能和顯能交互作用的過程,是個(gè)一邊“生發(fā)”、一邊“收拾”的過程。這種“生發(fā)”往往都是不可預(yù)計(jì)的,偶然的靈光忽現(xiàn),我們稱之為天機(jī),天趣。我們要懂得它的可貴,要不去干擾,不去涂抹,一任自,要保持這種不期而然的“出格”。
顯能的任務(wù)只是去調(diào)整,在收拾,不要走向兩極就是或者全部成為不可收拾或者加以理性抑止,以致生氣全無。我們要求任意“生發(fā)”,隨時(shí)“收拾”,心手相師。奇怪百變,出于意外而得乎環(huán)中。這種出乎意外的創(chuàng)造之美要靠適當(dāng)?shù)摹笆帐啊辈拍茏罱K完成。我想我又以中國藝術(shù)家自己的方式解讀了摩爾的潛能和顯能的結(jié)合的理論和實(shí)踐。
正因如此,所以摩爾作出了最終結(jié)論,“對(duì)我來說,抽象主義和超現(xiàn)實(shí)主義者之間劇烈爭(zhēng)吵是完全沒有必要的,所有好的藝術(shù)都是既包涵了抽象因素又包涵了超現(xiàn)實(shí)因素。正如它既有古典主義因素,又有浪漫主義因素一樣,包涵了秩序和出奇,理性和想象,自覺和不自覺,藝術(shù)家個(gè)性的兩個(gè)方面都會(huì)起它的作用。”我以為摩爾給我們的啟迪已經(jīng)夠多的了,我只想說謝謝這次展覽。五、一點(diǎn)補(bǔ)充本想結(jié)束了,但是摩爾精神感召了我。
我總想做得切實(shí)有效、更好一點(diǎn),因此就“潛能”問題再做些補(bǔ)充。“潛能”前文已說過,是人類的“本能”,是一種文化積淀。我體會(huì)到似乎起碼有五種因素。第一種是全人類在幾十萬年中積淀而成的,只要是人,那就必然擁有。譬如由“平衡”能力演變而成的對(duì)“平衡”的美感。這種屬于本能范圍的美感是一種不經(jīng)意識(shí)控制的反應(yīng)。我們見到垂直線就立即感到挺拔、剛直、向上;見到橫向水平線立即感到穩(wěn)當(dāng)、開闊;
見到斜線就覺沖刺力;波狀線就覺流動(dòng)、活潑,等等。這種反應(yīng)不需教育,人人都有。當(dāng)然有人說得出,有人說不出,但那反應(yīng)、感覺是差不多的。因?yàn)檫@種反應(yīng)是必然的,是不可抗拒的,我們就稱之為“形式規(guī)律”。這種規(guī)律存在于很多范疇,如體面的、明暗的、色彩的、音樂的,等等,都已有學(xué)者加以總結(jié),而它作用之巨大是驚人的,舉例如我們的天安門。天安門是明代封建皇帝為鞏固其封建統(tǒng)治而建造的,名為“天安”,當(dāng)然要體現(xiàn)王權(quán)永固安定如山。它的外輪廓就是金字塔型而去其頂,橫寬多于高聳,水平延伸,開闊雍容而內(nèi)部空間則是粗柱、遠(yuǎn)距、墻厚而門大,顯得雄壯而明朗。
這只是幾何體和空間的安排而已,但一種安穩(wěn)開闊泱泱大國的風(fēng)度已體現(xiàn)得淋漓盡致,明確無誤。而奇就奇在這天安門明為封建王朝所立,卻為無產(chǎn)階級(jí)政權(quán)所接受,毛主席于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huì)上即定此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徽,連名稱都不改,而那次大會(huì)集中了中國第一流人才,也都舉手贊成,一致通過;尤奇者是“史無前例”的“文革”期間,大破四舊,這個(gè)最大的“四舊”卻紋絲不動(dòng)。
推其原因,主要是“抽象的形式規(guī)律”起了決定性作用。因?yàn)檫@種比例線條,必然產(chǎn)生開闊穩(wěn)定之感,它并不由于階級(jí)、時(shí)代的不同而變化。它直接訴之于人的本能,而于意識(shí)形態(tài)無關(guān),這種“規(guī)律”、“本能”的力量是驚人的。“本能”的第二種因素是民族的。一個(gè)民族會(huì)有其特殊的“文化積淀”,比如中國人聽見喜鵲的叫聲,就立即很高興,覺的總有點(diǎn)喜事將臨,而外國人則一點(diǎn)反應(yīng)都沒有,鳥叫而已。外國老太太早上看見黑貓,則今天決不出門,以為不祥之兆。誰都知道,鳥和貓決不會(huì)管人類的禍福,但已成為“本能”不可抗拒。
第三種是時(shí)代的。在自然經(jīng)濟(jì)環(huán)境中成長(zhǎng)的人,見到農(nóng)村的破草房等,覺的有味道,入畫;見到抽水管道等等,就覺的不協(xié)調(diào),不畫。進(jìn)入工業(yè)化時(shí)代的人,對(duì)一切機(jī)械玩意都興趣盎然。法國蓬皮杜中心,即以管道見長(zhǎng)。這種一見就喜歡,一見就不喜歡,并不經(jīng)過理性分析,也屬“本能”反應(yīng)。第四種是階級(jí)的。
現(xiàn)在大都不提階級(jí)了,但依我看還是有的,農(nóng)民喜歡大紅大綠,封建文人就以為俗不可耐。這是客觀事實(shí)。第五種是個(gè)人長(zhǎng)期修養(yǎng)所形成的。長(zhǎng)期的訓(xùn)練可以形成“本能”,往往由知識(shí)變?yōu)榧寄埽杉寄茏優(yōu)橐环N職業(yè)反應(yīng),一種不經(jīng)大腦判斷而產(chǎn)生的“反應(yīng)”。張旭喝醉以后成為“草圣”;摩爾隨便使用“鉛筆、弄弄色彩和形體”就成了杰作;而普通人喝醉后就發(fā)酒瘋,弄弄鉛筆就出廢品。在這里,個(gè)人的長(zhǎng)期訓(xùn)練所形成的“本能”,是決定性的。同是本能但內(nèi)涵不同,質(zhì)量不同;
否則,以不動(dòng)腦筋為至上法門,豈非誤人子弟?其次:“潛能”調(diào)動(dòng)的可能性,一般來說,“潛能”的調(diào)動(dòng)都是不期而遇的,無從規(guī)劃的,不能控制,否則就不能叫做“潛能”了。呼之即來,揮之則去那還叫什么“不自覺”,“下意識(shí)”?但我的體會(huì),“潛能”既然是一種深層意識(shí),那就是可以激發(fā)調(diào)動(dòng)的,調(diào)動(dòng)的關(guān)鍵就是精神狀態(tài)的高度亢奮。亢奮得以至調(diào)動(dòng)最深層的“能力”,同時(shí)又要解除一切現(xiàn)實(shí)的束縛。中國書法家找到的辦法是喝酒,張旭、懷素都采用;
外國人好像是抽大麻等。但是這種辦法或者適合于一種爆發(fā)性創(chuàng)作,作業(yè)、作詩、潑墨潑彩、跳舞都可,但雕塑要長(zhǎng)時(shí)間地持續(xù)進(jìn)行,這辦法恐怕就不靈。建筑則更行不通,喝醉了的設(shè)計(jì),誰敢去住?那就只能靠長(zhǎng)期專注、念茲在茲,在持續(xù)的心無旁騖的勞動(dòng)中得到靈感的啟示了。但那高度亢奮和解除人為約束的前提是一樣的,調(diào)動(dòng)起來,都帶有偶然性,但偶然性的背后是必然性,也就是你的全部“文化積淀”包括個(gè)人長(zhǎng)期修養(yǎng)在內(nèi)。
我的貢獻(xiàn)只能如此了,謝謝你們的耐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