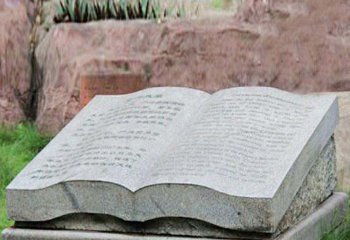作者:王朝聞“創作經驗談”收讀,更有助于我了解你的肖像雕塑。舊畫冊所錄的短文《吾將上下而求索》也很有意思,但遠不如新寫的“經驗談”談得全面和深入。讀“經驗談”可以幫助讀者讀懂你的肖像雕塑,理解你堅持正確的方向和藝術創造性的思想,肖像雕塑那嚴肅的題材和意象的獨創性為什么可能互相促進?人們未必理解肖像作品這種對立統一的關系。我這么強調你的“經驗談”的重要,并不是以為你的雕塑自身沒有這些可供觀眾發現的潛臺詞。

我不認為訴諸視覺的雕塑的潛在內容,只能依靠語言文字給它們作注釋,雕塑觀眾才理解雕塑自身的動人力量。但是讀你的“創作經驗談”,理解你如何上下求索的過程,也符合舊畫冊讀者需要。要是你愿意把它附入你的新畫冊,可以產生不是雕塑圖片所能代替的積極影響。

你接受的肖像創作任務,不見得創作素材都是已經熟悉的。外在的被動性的任務,為什么也可能轉化為主動性的創作激情?為什么作孫中山紀念像可能以現實主義戰勝自然主義?這一切,不是觀眾只憑觀賞雕塑作品的直覺所能理解得透徹的。肖像雕塑這一概念,已經規定了作品與像主的關系。但也如在你“經驗談”里著重談到的,往往有這樣一種現象,觀眾在第一印象中覺得很像,可看了參考照片后又覺得不很像,你不認為這是作品的失敗,而可能是觀眾的審美感受還有問題。這樣的分析不只反映了觀賞者的審美感受的矛盾,也反映了現實主義與自然主義的矛盾。

同意你所說的,只有形似而沒有神似的作品是不成功的。只憑我觀賞肖像雕塑或肖像繪畫的經驗,在同意你的認識的同時,也想另作一點補充。我從童年上私塾,就開始接觸那幅普遍流傳的孔子畫像。至今仍然沒有懷疑過,那一作品中的形象是不是像孔子的外貌。我雖知道孔夫子有一個生理特征——奔兒頭,但此外再也不知道他還有什么外貌上的具體特征。我一向不太重視孔子那奔兒頭的特征,正如我作毛澤東像從來不夸張他下巴上那顆突起的痣那樣。

我在童年時接觸孔子那幅肖像,曾有過一種畏懼感,感到老夫子的神態嚴肅。后來讀了他的《論語》,覺得他那不茍言笑的神態這一特征,和他在《論語》中與弟子們交談時的態度相互一致。如果傳說中的吳道子把孔子畫成笑嘻嘻的神態,在我看來就不太像孔子了。畫家閆立本那《歷代帝王像》中的帝王,他作畫時當然不可能是面對模特作寫生的,當然也沒有照片可供參考,更沒有可能在同一瞬間表現他們的后宮生活。

但我卻覺得,中國有些帝王的肖像越看越像。我這里所說的越看越像,是你也贊成的現實主義。20世紀30年代我在杭州藝專學雕塑,劉開渠先生在教室里給同學們的印象是不茍言笑的;但他和我談話,卻是知無不言的。他對我說過:肖像雕塑不必也不可能再現像主的一切生理特征;而且在若干年后,觀眾沒有可能憑他對像主外形的印象,當做判斷肖像雕塑像或不像的依據。劉老師對我的基本練習有嚴格的要求,和他主張肖像雕塑不必追求表面的像的見解并不沖突。40年代我在張家口為理解干部對毛澤東的印象,向熟人以至個別未見過面者作了許多訪問。
我這樣的意圖,是認為肖像雕塑不只應當表現像主自身的個性特征,也可相應地表現同時代人對像主的感受。這不是我的異想天開,而是40年代初,為延安中央黨校作毛澤東大浮雕像,當作品嵌入建筑早就留下的圓洞時,出現過學員們在現場先后不同的兩種反應:浮雕尚未安正而仰面朝天時,他們叫喊:“我們的毛主席不是這個樣子的!”當浮雕按原定設計安正時,他們說:“這還差不多!”因此,我覺得肖像創作的內容,應當相對地表現同時代人對像主的正確印象。順便指出:包括城市雕塑,例如深圳那只銅雕《開荒牛》,它既是城市的裝飾雕塑,又是這一城市創業精神的象征。
單就它的象征性來說,豈不相應地表現了同時代人的情感和思想。這樣談到我自己的經驗,不過為了說明我同意你那反對自然主義的主張。這種主張和紀念碑意義的肖像的永久價值有內在聯系。紀念碑性的肖像雕塑,究竟有沒有相對性的永久性的生命力?
我看是有的。你在創作過程中,參考像主的某些照片時,排除照片上的偶然性因素,這也是以雕塑作品可能引起什么反應的預見為條件的。值得為你也為觀眾高興的,是你一貫不追求時髦,不見風使舵,沒有把迎合低級趣味當做所謂時代精神。時代精神這一概念,立場不同者往往賦予它不同的涵義。你的近百件作品具有你所掌握的時代精神,而且它們的共同風格,是在質樸無華的形式里顯示了獨創性的。單就你為不同個性的烈士紀念像選擇紅色或白色的石頭這一點看來,你很重視像主的個性可能在觀眾中引起什么特殊感受。
因此可以認為,雕塑家的藝術個性,與像主的個性在作品中的表現,可能既有差別也有一致性。風格的質樸性是以非自然主義的創造性為前提的。你那正確的方向與道路,和人物個性的多樣化的關系,既是對立的也是統一的。余容面談。祝愿你在接受新的命題創作時,像并非本色演員那樣,在默戲時更深入地進入各種角色,也就是為各種肖像雕塑的成功,繼續塑造自己的藝術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