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下旬,一個在古都南京的博物館舉行的小規模“實驗空間現代藝術展”,因當地媒體一篇名為《女生自拍下體圖片在南博展出》的報道,成為一則“熱鬧”的社會事件。該作品瞬間變成展廳的焦點,不少當地居民聞訊前往博物館一觀究竟,經網絡轉載后,一時間在網上網下引起關乎道德的激烈討伐與謾罵。劉海粟的人體模特在中國“試法”至今近百年,在藝術形式日漸多元和社會呈現角度更加豐富的今天,還有如此多的人甚至部分輿論在糾纏所謂藝術與道德的關系,也許該反思的不是藝術工作者,而是那些對此提起道德謾罵的人。王桂權剛注冊了MSN,隨即把MSN的名字改成:萬物皆生靈,不可以隨便傷害。

這個被網上風傳“自拍下體”的大學二年級女生感到,在剛剛結束的南京畫展上,自己被傷害了。王桂權就讀于川音成都美術學院油畫系,師從德國籍華人畫家王承云。2005年9月,在成都藍色空間畫廊,畫家俞曉夫、王承云、鄧箭今等三人的作品進行聯展。在展覽會的酒會上,四川畫家何多苓領著一個年輕的女孩跟王承云說,“你是外國人,我再給你介紹個外國人。

”這個女孩名字叫禾子,也是華人,生活在丹麥,長期關注中國油畫及各種藝術。很快,大家成為朋友。在禾子看來,王承云是個很有意思的人,一喝多酒就會現場跳舞。2005年冬天,在北京一家畫廊的畫展上,禾子再次遇到王承云。王承云向她談到了自己的教學計劃,越談越興奮,他認為自己的教學方法在中國具有實驗性。其實,在歐洲這樣的教學方法很多。禾子說,在丹麥,甚至從小學到中學的10年義務教育中,實行的都是無課本教學。

學生經常在課堂以外的公共場合上課,比如博物院。所以,王承云說這個教學方法時,她一點都沒覺得特殊。只不過,這樣的教學方式,在中國是很少見的。據禾子觀察,王承云的每個學生,都有各自明顯的風格。禾子說,藝術品是要拿出來看的,你可以把你學生的作品展示一下。當時,王承云正在到處找畫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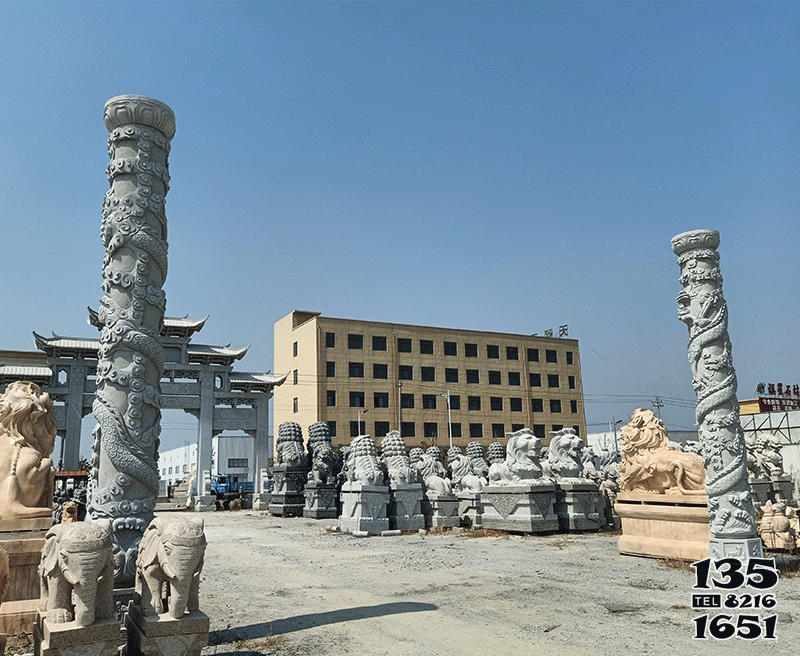
禾子說可以幫他搞一次畫展,“這些學生沒有參加過畫展,給他們一點小小的經驗。”4月21日下午開始——好像畫展都是在周末下午開展的,這個名叫“實驗空間”的畫展,在成都畫廊免費試展了一個星期。當時,禾子在丹麥有事,沒去成都。這次試展,并沒有人把注意力放在王桂權的作品上。

只發生一個小花絮:當地記者們對另一個作品比較感興趣——同學胡曉波制作的兩件2米多長的陽性軟雕塑和小的生殖器的裝置,有記者追問了一個“出格”的問題,胡曉波一時回答不出來,紅著臉轉身沖王承云喊:“王老師,流氓!”這句話演繹成了朋友們對王承云的一句玩笑“王老師——流氓。
”王承云說,聯想到女孩子在中國的地位和感覺,胡曉波幽默地作了這樣一個陽性玩具,人們可以睡在上面,可以玩耍,甚至擊打它——那已經不叫生殖器,整個意義全部都改變了。這次試展,在成都的反響不錯,媒體給了正面的報道,觀眾的態度也很平靜。王承云原想把這次展覽在北京或上海巡展,禾子沒有同意。
之前,禾子剛在南京博物院搞過一次“南京——成都新銳畫家作品展”,對南京的展覽環境比較熟悉。她隨口對王承云說,“南京出名后,就全國出名了。”——后來,當王桂權的作品引起爭議后,王承云在電話中向禾子說,“被你說中了,我實在受不了啦。網上有人說我是‘人渣’。”這次展覽,沒有做任何廣告,沒有請媒體,只告知了圈內畫家和南京美術專業的學生們。禾子說:“我們的初衷很簡單,就是一個教學實驗的展覽。
”南京博物院只負責出租場地,不負責藝術展覽的內容。但博物院很支持這個展覽,甚至為此推后了另外一個國畫展。5月16日,王承云發短信給禾子,學生們16日上火車,18日到。從成都到南京,要坐兩天多的火車,30多個小時。學生買的是慢車硬座,沒買臥鋪。5月18日中午,班上24個學生出現在南京火車站。
禾子把他們安排在青年旅社,簡單洗了一下,沒有休息,就去布展。由于之前沒有去成都參加試展,當打開包裝發現王桂權的作品時,禾子微感突然,但并沒有覺得有什么不合適。剛開始時,學生們把胡曉波的2米多大的陽性軟雕塑掛在一進展廳的柱子上,背景是白墻,在他們看來,這個象征力量,很喜慶。博物院領導看到說“哎呀,這個還蠻有意思的嘛!
”由于展廳緊挨著辦公區,第二天上午,博物院的辦公室主任朱曉光打電話給禾子說“我們這里都是老學者,他們接受不了,都找到院領導那里了。”“禾子,幫幫忙吧,能不能往后掛一下。”開展第一天,南京《金陵晚報》的文化記者羊艷,聽朋友說博物院有個畫展,就來觀看。看了一會,她并沒有注意到王桂權的作品。
快要走時,看見有一個男孩和一個女孩在作品前談論。男孩是一個觀眾,他說,我來這里,就對兩幅作品感興趣,一個是軟雕塑,一個就是這個作品。女孩就是作品的作者王桂權。羊艷問,這個作品怎么啦?王桂權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當時,她反問了羊艷一句說:“你看了作品,感覺是什么呢?”接著,她對羊艷說:“如果你看不懂的話,就當作一面鏡子看你自己。
”按照王桂權的陳述,羊艷在后來的報道中把自己的話寫錯了。在羊艷的報道中,這句話是“其實很簡單,我最初我只是想看清楚鏡子里的自己是什么樣子。”擺在羊艷面前的作品是,很多條繪著花的衛生紙搭起來,中間的墻壁上掛著王桂權對自己陰部的幾幅自拍照片,地下還有一些衛生紙。只不過,照片上加了顏料,所以,人們一般看不出照片上是什么,許多人認為這是有著旺盛生命力的草。經過王桂權的解釋后,羊艷覺得這是一條很好的新聞。
她寫了篇稿子,標題是“女生自拍下體圖片在南博展出”。第二天,王桂權給禾子發了一條短信:“剛才我得知了《金陵晚報》報道了我們的作品,看后我很生氣,我覺得他們完全誤解了我做作品時的思維方式和我想表達的意思,他們這樣的報道我真的很不能理解和不開心,所以禾子老師我需要你的幫助,謝謝。”此后三天,羊艷作了3次相關報道,引起了南京對此展覽的大討論。文章上了報社的內部網,被其他網站轉載出去,迅速成為網際新話題,點擊量快速攀升。王桂權的作品在現場70多件作品中脫穎而出,成為一些輿論在談及此畫展的代名詞。
緊接著,許多并不喜歡藝術和不懂油畫的人紛紛去看展覽。剛好不收門票,有幾個老年人一而再再而三地進去觀看,被保安發現后,阻止再次進入。也許是城市文化的不同,胡曉波制作的陽性小藝術品,成都展覽結束時賣了很多,自己還掛了一個在包上,并沒有招來多少異樣的眼光,但在南京卻被大驚小怪。在展廳,本刊記者看到,王桂權的作品前有一個臺子,由于之前人們為了湊上前去看得仔細一點,老踩上去,工作人員不得已在臺子前拉了一條線攔住。
每天,都有許多讀者打電話給《金陵晚報》,參與討論。羊艷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當時有個奇怪的現象是“許多老年人表示能接受,年輕人則大罵。”展廳現場,一位老先生告訴羊艷,著名畫家劉海粟當年畫人體,引起了軒然大波,幾十年后,人們都認為他是大師。這位老先生說:“說不定這個作者將來也可能是大師。”因為現場沒了解說,許多觀眾在展廳里找不到這幅作品,便打電話給報社,“你們做的是假新聞,現場沒有這幅作品啊。
”5月26日,一個觀眾不知道從哪里找到了禾子的電話號碼,他打電話給禾子時,語氣很嚴肅,聲音聽上去有50多歲。他稱自己給王桂權寫了一封信,向禾子要王桂權的地址和電話號碼。禾子說可以轉交后,這個人說了個地址,要求禾子過去取信,“我也順便想跟你聊一些展覽的事情。”禾子拒絕后,他很生氣地說,“有一些東西是要撤掉的。
”當禾子告訴了自己住的酒店地址,這個人說“你還蠻有錢的嘛!”“真不知道這些人是什么想法?”久居歐洲的禾子對這個人的心態完全無法理解。還有一個人,據說從《金陵晚報》熱線得到了禾子的電話,要向禾子買畫。“你買它做什么,”“這個你不用管。”禾子說,不賣。
對方說,你們展覽不就是為了賣嗎。5月29日,展覽結束,幾個農民工被找去幫忙撤展。他們進去后,把搭在王桂權作品上面的紙不由分說扯了下來。在撤陽性軟雕塑裝置時,民工低著頭,看都不敢看,紅著臉說“那是什么啊”。禾子說,算了,算了,你們走吧,我們還是自己撤吧。在打包往成都郵寄時,工作人員按了一下袋子里王桂權的紙作品后說,這不是垃圾嘛。禾子趕忙解釋說,這可是藝術品,別弄丟了,弄丟了,我可賠不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