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聽說這次您是受邀來策劃這次展覽,您一直在北京生活,在那里也舉行過多次的展覽,那么這次上海雙年展和您以往參加的展覽有什么不同?黃篤:我認為區別還是很大的,首先上海雙年展的視野是全球性的;第二,她的測展團隊也是國際化的,這些策展人來自韓國,意大利,英國,美國等不同的國家,所以說上海雙年展是一個大的國際化的項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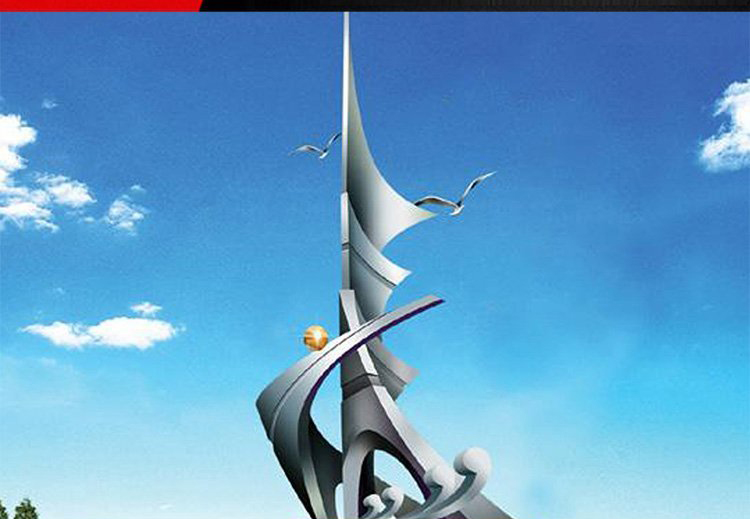
第三,讓我們回到展覽的主體——藝術家上面來,這次上海雙年展國際化的隊伍有個很大程度的加強,國外藝術家的比例占到了近70%。這些藝術家也來自美學的各個不同領域,比如:錄像,攝影,裝置,多媒體,還有傳統意義上的繪畫。以上這些是從媒介方面的不同,當然還有觀念上的不同。例如:有的藝術強調一種生活方式,有的強調文化上的跨越等,這都是與普通展覽所不同的地方。

上海雙年展帶給我的挑戰性也是非常大的,因為要協調包括美術館,策展人,不同國度藝術家等多方面的人員。記者:我們知道北京和上海是中國的兩大城市,北京又是中國的文化中心,而這樣一個國際化的大型藝術展會在上海舉辦,您認為有什么原因在里面?黃篤:首先我在這里需要強調一點,北京也有雙年展,但是北京的雙年展和上海雙年展是有所區別的。北京的雙年展在框架上以美學為組織方,基本上沒有策展人這種制度。而上海雙年展更強調新的動態,以及前沿文化的實踐。

而上海作為中國的一個經濟龍頭,在亞洲甚至全球的地位都是十分重要的。所以上海在文化方面更加的開放,更加的包容,更加了解國際文化的轉向。所以,歷屆的上海雙年展代表了一種超前的意識。這也是其一個鮮明的特點。此外,在技術支持和組織結構方面,上海雙年展有一個很專業的團隊。

所以在這些方面,上海要比北京更加的成熟,更加的有經驗。例如:在選擇策展人方面都是經過了深思熟慮,之前對策展人的背景進行了深入的了解,而且和策展人也進行了多方面的溝通。所以說,上海在這方面更有國際化的眼光。記者:那么在政府支持方面,北京和上海有什么區別嗎?黃篤:我覺得兩個城市的政府都給予了相當大的支持,包括撥款,預算方面。但是隨著展覽規模的逐步擴大,以及技術越來越復雜,之前做的預算很可能會遇到障礙,這也使得任何一個展覽都遇到財政方面的問題。

例如新加坡雙年展的預算高達2億人民幣,而韓國雙年展也達到了近1億人民幣。這就需要使我們不要把眼光局限在政府方面,更多的要放在企業和公司上面。只有這樣雙年展才可能更加的靈活。此外,現在政府也逐漸意識到文化的繁榮對于經濟的發展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也大力提倡國與國之間的文化交流。
記者:現在藝術交流是否只通過展覽這種方式,還是有其他別的方式,例如媒體?黃篤:首先我認為國內的媒體在這方面做的不是很好,國內的電視臺娛樂方面的傾向是比較嚴重的,可能是由于這方面的內容比較吸引眼球吧。而在德國,韓國等國家,雜志,報紙,電視臺等媒體對藝術家的關注程度比較高,而國內的媒體就處于一個比較尷尬的境地。例如,我們的媒體對像幾米這樣的大眾化的明星藝術家比較關注,而不會去關心一些很冷靜,很抽象的作品,這說明在專業方面和美學方面還是缺乏一定的思考。我們媒體記者在專業知識方面也是比較的缺乏,而一些歐洲的藝術記者,他們對藝術方面非常的了解,而且對一些藝術現象也有自己獨到的見解。
但是,像雜志,報紙,網站等媒體是非常重要的,而如何去報道也是一門很專業的學問。記者:上海雙年展相對于同時在新加坡和韓國舉辦的雙年展有什么自身的特色?黃篤:新加坡雙年展的主題是“信念”,其主策展人是南條史生,其策展人主要來自東南亞地區。南條被選為新加坡雙年展的策展人某種意義反映了日本政治文化的走向,一直以來日本的策展人想從文化角度在亞洲建立日本文化龍頭老大的地位。這與日本的地源和東南亞的文化語境是有一定關系的。
當然日本在東南亞地區的文化影響力還是很大的,這是以日本國家交流基金會為基礎和支柱的。而光州的雙年展相對來說比較抽象一些,主題是“熱帶變奏曲”,其策展團隊相對來說還是有些保守,而主題方面也顯得不是特別明確,其原本想探討城市之間的一種關系。而上海雙年展存在兩條線,一條是藝術史,另一條是從上海自身發展邏輯的層面。所以說在這三個雙年展中,上海雙年展是最為開放的,包容性也是最強的。上海雙年展是一個視覺藝術的展覽,而不是一個純設計的概念展覽。
但是我們要挖掘設計本身所蘊含的能量,而不是要做一個功能性的設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