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從“建筑藝術”的文化性和中外文化的不同,論述了中國建筑應立足于本國文化土壤之上,慎言與西方的“接軌”;從建筑的雙重性和建筑藝術的層級性、公眾性,論述了“建筑藝術”只是指稱建筑中的“藝術性”。“建筑”作為整體,不可能是純藝術,仍應以滿足包括功能在內的物?內容提要:作者從“建筑藝術”的文化性和中外文化的不同,論述了中國建筑應立足于本國文化土壤之上,慎言與西方的“接軌”;

從建筑的雙重性和建筑藝術的層級性、公眾性,論述了“建筑藝術”只是指稱建筑中的“藝術性”。“建筑”作為整體,不可能是純藝術,仍應以滿足包括功能在內的物質性為其首要的追求,慎言“藝術”。《建筑師》前些年連續發表了張良皋先生的《建筑慎言“個性”》和關肇鄴先生的《建筑慎言“創新”》,討論了一些很重要的議題。筆者追隨兩位前輩,試著就建筑的“接軌”與“藝術”兩個問題也略作探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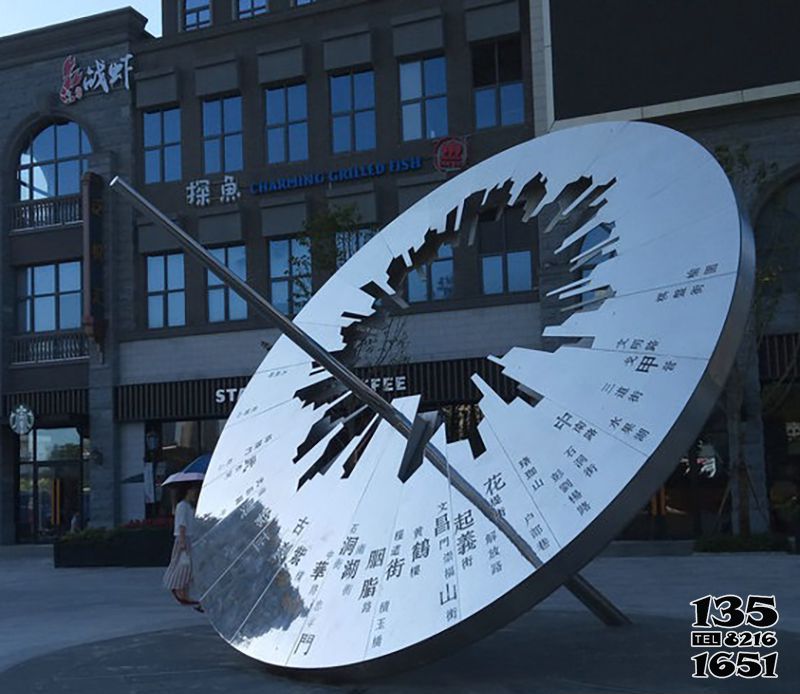
我想,就中國的國情和建筑現狀來說,多提提“慎言”,還是不無意義的。建筑慎言“接軌”提到“接軌”,首先想到這多半是一樁好事。作者在印度考察時,陪同的辛格先生就對我們的秦始皇特別欽佩。他說,秦始皇硬性推行“書同文,車同軌”,還統一了度量衡,促使中國早就成了一個大一統的國家,而與秦始皇幾乎同時的印度阿育王卻沒能做到。
所以印度在1948年獨立以前,就從來沒有真正統一過。直到現在還存在這個問題,使用最多的印地語的人口只占全國的40%,不得不拿英語作為事實上的國語。而統一自然有利于國家的穩定和發展,看來,“接軌”的確是好得很了。但仔細一想,先秦的中國本就是以華夏民族和華夏文化為主體的一統地域,戰國“七雄”不過是在這個大格局下分立的一些諸侯政權,上面還有一個周天子。
秦朝的統一很大程度上只具有專制政體確立的意義,還要靠軍事征服和例如郡縣制等制度的推行才得以實現,不能完全歸功于“接軌”的。重要的是,這類事也只能就此打住,如果無限地延伸開來,以“全球化”為借口,任什么東西都來一個全球大接軌:只有一種文化,只用一種語言和文字,把春節與圣誕節合并,再設計出一個標準人種,不黃不白也不黑…我看,這無疑有如囈語。在中國,也不會有任何正常人會想到要把56個民族都“接軌”成一個民族的。所以,“接軌”理當慎言。
全球化與多元化,本就是一件事的兩個方面,同時存在,互為前提,相輔相成,不容偏廢。但卻總是有一些人士,不設前提,不論范疇,不管成敗,天天都在那里高喊要與西方“接軌”,僅就建筑而言,就本人所知,最近也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文學理論家也是筆者的老相識葉廷芳先生的主張了。葉先生以包括備受爭議的國家大劇院且已被證明失敗了的其他建筑為例,贊揚“我國在這方面也確實與世界接軌了”,因為這些建筑“都實行國際招標,并都讓外國高手們中了標”。
認為“不管成敗如何,這個開頭是值得肯定的”。葉先生的理由是“各國建筑師的跨疆越界,被邀去他國設計一些重要的,甚至是國家級的標志性建筑,早已司空見慣,成了國際慣例。不一定非要自己的建筑師出來一顯身手,也不一定要以本民族的傳統風格為基準。只要這座成功的建筑物聳立在你的土地上,就顯示了你作為業主的慧眼和格調,你和你的祖國就獲得了榮譽”,“現代建筑像象其他藝術一樣是不認國界的”,“關鍵是人們有個平和的心態”,“告別爭吵”①。
這些話,還有葉先生全文的許多立論,要仔細琢磨起來,恕本人直言,問題實在太多。先不說別的,現代建筑藝術真的是“不認國界”么?爭吵誠然應該告別,爭鳴還是要有的。什么是“藝術”,雖然說法不少,但絕不僅是葉先生只提到的“好看”或“美觀”。廣義的“藝術”可能與“好看”有更多關聯,但真正的或稱狹義的藝術,按俄國啟蒙主義美學家車爾尼雪夫斯基的著名論斷,是除了在“優雅、精致、美好的意義上的美的東西”也即“好看”以外,還需要“更多的東西”的②。
這“更多的東西”,依鄙見,首要的該就是“文化”。由這個角度,談“藝術”實質上就是在談“文化”——而“文化”,恰恰是最認國界的。古代世界,要細論或多或少或長或短發揮過作用的文化,少說也有幾百種,毫無例外,都有其流傳有緒的國家、民族或地域的界限。最重要者公認為三種,即儒家文化、基督教文化和伊斯蘭文化,分別流傳在東亞、西方和伊斯蘭地區,從來都是“有界”的。文化是各文化圈的人們在共同生活中歷經千百年長期積淀出來的,自然有很強的傳承性,這三大文化就一直傳到現代,仍然有界。
例如以原初儒學為主的中華傳統文化,幾千年來,雖屢遭異化,近百年來,更成了中國主流文化的痛打對象,無辜地扮演著負面的角色。但幾上幾下,卻始終也打不死,竟仍深蓄于現代中國人的心底,且大有復興之勢。現在提倡的以人為本、和諧社會等觀念,也不能說與它無關。
世界上文化的發源地四大文明古國——埃及、兩河、中國和印度,只有中國文化歷5000年而傳承不斷,也不能不說有賴于原初儒學之所賜。產生較晚的伊斯蘭文化也不待說,即如基督教,古代雖有多達兩百個教派——分屬于天主教、東正教、新教,還有單獨成派的,到了今天也大多并未消失。
無論何派,仍都以希伯來人創立的原始教義如原罪說、救贖說為中心,成了西方文化的根基。這些傳統對于現代世界仍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隨著各國現代發展進程的不同,新析出的文化因子也必有不同,故總體來說,世界各國的文化是更加豐富更加多樣了,怎么忽然就“不認國界”了呢!藝術當然離不開審美,中華優秀文化傳統對中國人的審美觀就有著深刻的影響。中國傳統建筑強烈顯現的人本主義、注重整體的觀念、人與自然融合的觀念、“百舉不過”的觀念、重視與地域文化的結合,以及許多具體處理手法如建筑的群體布局、特色鮮明的空間構圖和造型手法、建筑的環境選址及“雖由人作,宛自天開”的優秀處理、獨特的色彩表現、裝飾與功能的結合及其人文性…
等等,在在都與西方人之強調單體的突出、與自然強烈對比,而不太著重于群體及與環境的和諧不同。要往深里追究,這里面的說頭就更多了。憑什么中國人一看到葉先生多次推崇的蓬皮杜中心和畢爾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館,就必得拋棄自己的一切美學傳統,而與其“接軌”,以顯示自己的“慧眼和格調”、“獲得榮譽”呢?
照此邏輯,若然是中國人居然膽敢不予“接軌”,那就是“慧眼”全無,“格調”低下,恥于為人了!其實,葉先生推崇的這些建筑大多并不是什么好東西,即便在西方,至今也仍備受責難。它們的怪異,正是西方審美觀在當代“張揚個性”思潮下的惡性膨脹。前者以“高技”為賣點,其實其所有技術在別的建筑中全都用過,談不上更“高”。那些披掛在立面上的管子也令人起疑,太多也太粗,其中定然有詐,有一些不過是一種虛假裝飾而已。西方不少評論家直到現在還批評它是一種“波普派烏托邦大雜燴”,是“一架偶然降落在巴黎的班機”。
蓬皮杜總統在國民議會對這座建筑曾表達過愿景:“我愛藝術,我愛巴黎,我愛法國。這個中心應該是表現我們時代的一個城市建筑藝術群組,要搞一個看起來美觀的真正的紀念性建筑。”但建筑落成時蓬皮杜已經逝世了,人們已不可能得知他對于這個中心是否達到了他希望的應該是法國的、巴黎的和藝術的、時代的評價了。至少眼拙如本人者,若是不事先告知,是不可能看得出來的,因為它正是“不分國界論”的產物。
畢爾巴鄂的那座建筑自稱“解構”,表現了作者對現代主義建筑理性主義的總體性懷疑,否定建筑的整體性,只對部件感興趣。把整體打破,再把部件重新組合,形成一種所謂“解構”的形態。“解構主義”本身原是一種哲學,由法國哲學家、1968年參加過法國“五月風暴”的德里達宣揚開來的。這種哲學實在難懂,當時就有多達20位哲學家宣稱讀不懂它,聯名反對劍橋大學授予他學位。而且這種哲學本與建筑毫無瓜葛,硬要將它引入建筑的“大師”艾森曼對它作過解釋,詞兒挺多,卻越說越讓人一頭霧水,如同乩語。
觀眾問過1988年紐約一次解構主義建筑展覽會的主辦者倒底什么是“解構主義建筑”?他只是說不是這個,也不是那個,更不是第三個,那么到底是哪個?卻總是追問不出來。看來連他也不懂,只不過以展覽為幌子,賣門票賺錢而已。對于這種無法無天的“主義”,甚至連第一個提出后現代主義口號的詹克斯也看不下去了,以至于說艾森曼之信奉解構主義與艾氏之接受精神病治療“這兩件事無疑相互影響”。
此意至明,無須再說。以上所謂“高技”或“解構”,還有當代西方各種各樣無以理喻的種種“主義”或“流派”,不妨都可統稱為“先鋒派”。有位藝術理論家從當代繪畫和雕塑的發展過程分析了先鋒派現象:當代藝術一步步從宗教、政治、歷史、事件、哲學、文學的依附地位中解放出來,變為不依附于其它任何事物的“自身”;一步步從“現實的影子”中擺脫出來,變為一種純造型的努力。經過古典主義、浪漫主義、印象主義、后印象主義、立體主義、野獸主義、表現主義、抽象主義…
一步步失去了一切,最后,只剩下了一些抽象的點、線和面,再也走不下去了!為了為這種藝術尋找出路,給《蒙娜麗莎》畫上了兩撇小胡子的著名玩家杜尚忽然發現:“原來現成品就是藝術品——只要人們用藝術品的態度去對待它;原來藝術品也就是現成品——只要人們用現成品的態度去對待它”。
順著這條思路,結果是,杜尚“創作”出了最驚世駭俗、最褻瀆文明、最歹徒、最有代表性也最“成功”的作品《泉》——一個小便器。不是他雕塑出來的,就是直接從雜貨店買來的,他只是在上面簽了個名③。所以,詹克斯的話對我們來說,至少有某種啟示意義,就是對于時下這些高深莫測的先鋒或先鋒理論,其實多半都屬炒作,大可不必太認真,尤其不能輕信,更不宜奢談與其“接軌”。
而葉先生向我們推薦的在中國出現的由“外國高手”設計的東西,包括“鳥蛋”、“鳥巢”、“鳥樹”、“鳥籠”和由以“解構”而自豪的英國人哈迪德以“圓潤雙礫”命名的廣州歌劇院,也都是這一類追求新、奇、特、怪、洋的物件兒,其推薦的理由便是未加論證的“藝術沒有國界”。但平心而論,這句話也并非全錯。西方各國,原本文化就是一體的,都屬于兩希文化圈,自古建筑就大體相同,早就“跨疆越界”了。各國國情,至今也大體相似。而中國文化與國情與他們的差別大矣!豈可與西方各國混同?
中國地域廣大,不但要與西方分出國界,國內還要有族界、地界,才能顯出足夠的多元和多樣。尤其碰到聲稱要把中國文化“推到危機的邊緣”和一到中國就說出“難道周圍都是狗屎,我也要與它協調”等狂妄之語而不懷好意的“外國高手”,更要加倍小心。我真的想不通為什么我們不早一點炒了他們的魷魚。
前已提到的國情,必然也是考慮“接軌”與否的重要前提。有人說,中國雖窮,為了給自己打點一下臉面,搞一點這種東西還是可以的。依我看正好相反,這些“外國高手”搞的這么些個東西,只會給中國人臉上抹黑。比如說我要接待一位貴客,是勉為其難地先買上一套高檔法國沙發,放在我四面透風的土屋子里,孩子們卻面露菜色,因為買沙發把錢花光了,家人也都蓬頭垢面,更能給我爭來面子呢?還是把透風的地方先堵上,讓孩子們營養充足一些,露出天真的笑臉,全家人都理個發,穿得乾凈一點,房子收拾得窗明幾凈,更能給自己贏得尊嚴呢?
如果這位客人贊賞我的第二套方案,說明他值得交往;如若不然,只因為我沒有法國沙發就瞧不起我,那就隨他去吧,不交也罷。說到沙發,倒想起了一件真事。上世紀“文革”晚期我還在敦煌的時候,英國著名記者韓素音要來,縣革委會派出專車趕往鄰縣拉回一套高檔沙發,擺到剛剛被“解放”的常書鴻先生住了三十幾年的小土屋里,把常老自砌的也有些年頭的土坯“沙發”打掉。常老從蘭州回來,大發雷霆,但也莫可奈何了。
至今想起,仍深為常老的自尊而感動。這種事,道理簡單至極,完全無需理論家來論證。“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葉先生向我們推薦的這些東西,到底值不值得如此肯定,還是讓事實來說話。這里只須引用一些評論就夠了:據人民日報記者吳焰2007年2月9日報道:由安德魯設計、耗資超過11億的上海東方藝術中心,“這個力求與國際接軌的大型劇場,給管理運營方提出了新考驗。以保潔為例,裝飾東方藝術中心內墻的陶瓷掛片多達15.8萬片,最高處達14.8米,全部擦洗一遍就要兩個月;
4700塊玻璃幕墻‘外罩’,每洗一次得4萬元。電費更占‘東方’全部開銷的1/3,平均每天維護成本就達9萬元”,“冰上舞臺則很少啟用。去年夏天,俄羅斯圣彼得堡國家冰上芭蕾舞團曾首次啟用,讓觀眾嘆為觀止,可使用也只此一次。豪華設施為何閑置?以冰上舞臺為例,它每啟用一次,僅耗冰成本就達2萬元,更重要的是目前國內尚無冰上芭蕾舞團。
而管風琴對環境要求更高,需要整個音樂廳24小時的恒溫、恒濕,光是電費就是一個驚人數字”。據報道,東方藝術中心為了體現以人為本,限制票價,最高價卻已達4000元。但管理者還是覺得很委屈:“票房收入近700萬元,僅及成本的一半多。”最后當然只得主要依靠政府買單來擺平了。這種情況絕非個例,人民日報一下子就點了七家劇院的名,還不包括也必將如此的國家大劇院和其他建筑。
網友們寫道:“我們要問的是,這樣的藝術中心建起來之前,有沒有經過專家充分的評估或論證?”這使我想到,早在2000年年中,關于國家大劇院的幾封民間上書就對有關方面提出過“不知有何科學依據,是否經過認真的論證”的質疑。后來證明,果然直到開工那一天,都沒有經過認真的論證,以致原定2000年4月1日進行的隆重的開工典禮不得不臨時取消了。人們不明白是什么原因,直到同年9月,通過鳳凰衛視,才從一位業主委員會成員嘴里,得知是因為“它的可行性研究報告還沒正式批復”。
而可行性研究報告正是論證的結果,它的編制及其批復本該在立項、撥款、編制設計任務書之前就完成的,然后才能談到招標、設計,最后還要經首規委、市計委、市建委審核,發放開工證,方能輪到開工的。本人在《城市規劃》2001年第5期發表的《依法治國──四評安氏國家大劇院方案》中就據此寫道:“人們有理由質疑,設計任務書確定的規模,包括四座劇院的劇院群外加許多其他功能,是不是經過了規劃法要求的嚴格論證?
”而有關造價與票價問題,在當時的爭論中也是焦點之一。本人在同一文中就提過:“從許多文章的分析中,人們得不出樂觀的結論,可能將永遠收不回成本,永遠需要國家的巨額補貼,成為中國人民一個甩不掉的包袱。何況,能夠享受這種高檔消費同時也得以享受國家補貼的人士,肯定不會是普通平民,由此造成的政治影響,操作部門是否也考慮到了呢?”不是說要“講政治”嗎?無須再多費筆墨了,不管葉先生還要以“藝術”或別的什么美好的名義向我們推薦什么東西,吃一塹長一智,中國人和中國政府已經更加理智了。今年1月,由建設部和發改委等五部委聯合發布的《關于加強大型公共建筑工程建設管理的若干意見》已對“一些地方不顧國情和財力,熱衷于搞不切實際的‘政績工程’、‘形象工程’;
不注重節約資源能源,占用土地過多…甚至存在安全隱患”作出了嚴厲批評。提倡“以人為本,立足國情…項目投資決策前,建設單位應當委托專業咨詢機構編制內容全面的可行性研究報告”。文件還特別強調,要鼓勵“自主創新”,規定“建設單位應立足國內組織設計方案招標,避免盲目搞國際招標”。那么,“接軌”還要不要呢?
我得回答當然需要,但卻是有前提的,有范圍的。即便這樣,必要性與可能性也不是一回事。比如火車軌距,由于歷史原因,至今全世界還有30多種規格,窄者610毫米,寬者2141毫米。同在中國,由于最初的鐵路大都由列強分建,還有軍閥割據,軌距也不相同,當然造成了運輸的困難。盡管早在1937年各國就作出過決定,以1825年英國人斯蒂芬森最早根據古羅馬戰車的寬度1435毫米為國際標準軌距,但要全部都改過來,卻談何容易!
至少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是辦不到的。所以,在軌距不同處,人貨至今還得轉移車廂。聰明人又想出了一種可變輪距的主意,以實現國際聯運,同樣得假以時日。這類事,還有其他一些本來就沒有國界的如科學技術,就可以稱為“接軌”,也不是都能說接就接的。有的人家還不讓接,保密;有的中國有意不接,要保有自主創新的知識產權。
另外一些事,大者如重大體制的改革,次者如建筑藝術,小者如公交車牌的樣式,則不妨稱為“借鑒”,似乎更加確切。還有些事兒,比如是吃面包牛奶還是吃饅頭稀飯,我看連借鑒都不必,隨著性子來就行了。建筑慎言“藝術”葉先生為證明與西方“接軌”之必要,武斷地判定中國建筑理論一直比西方“滯后”,說中國直到漢代才有了一部與建筑有關的《考工記》,晚于公元前1世紀維特魯威的《建筑十書》。依拙見,以某本現存書的出現早晚來定案這件事,并沒有多少說服力。不論中外,佚書之事所在多有。
事實上,中國建筑理論至遲早在公元前5世紀春秋、戰國之交就已經發軔并達到相當深度了,儒、法、老、墨和堪輿家對此都發表了看法。儒家特別重視文藝的社會功用,強調建筑的精神性方面,第一次以理論的方式表明了人們對建筑藝術的自覺。
《禮記》就認為:遠古本來沒有建筑,人們冬天住在地穴里,夏天住到樹屋上…以后,“圣人”熔煉了金屬,燒制陶瓦,才造成了臺榭、宮室和門窗…用來接待神靈和先祖亡魂,嚴明了君臣的尊卑,增進了兄弟父子的感情,使上下有序,男女界限分明。這就把建筑的出現,歸結為懂得禮樂法度的“圣人”的建制,而且一下子就提到了精神倫理的高度。法家的觀點主要反映在《管子》中,強調建筑的物質性方面,主張一切應從實際的物質需要與可能出發,不必中規中矩。墨家與法家相近,認為建筑只要“高足以辟潤濕,旁足以圉風寒,上足以待霜雪雨露”就行了,“便于生,不以為觀樂也”。
它們都對實踐發生過作用,例如《禮記》提出的“中正無邪,禮之質也”就對強調中軸對稱的建筑群布局產生過很大影響。儒家還繼承和充實了源于原始祖先崇拜和自然神崇拜的觀念,成為中國建筑獨有而歷久不衰的禮制建筑的濫觴及重視帝王陵墓建設的導因。儒家提倡的“中和”、“溫柔敦厚”、“百舉不過”等中庸思想,也對中國建筑藝術的風格產生了持久的影響。
孔子基于“仁學”首先提出來的“卑宮室”思想,得到了法家和墨家的響應,對于扼制統治者的過度奢華,也起過有益的作用。他們分別論述了建筑的物質性與精神性,接觸了建筑的本質,較之維特魯威,其深度已遠遠超過,不可同日而語了。但直到今天,對于建筑的雙重性問題,仍存在一些理解的誤區。
一者近于只承認建筑的物質性,對于精神性,認定不過只是“美觀”而已,只需要“在可能條件下”“注意”一下子就得了,忽視某些建筑也可能和有必要擁有具有一定深度文化內涵的“真正的藝術”品性。另一者則只強調其精神性,將各層級的“建筑藝術”甚至“建筑”的整體不加區別地完全等同于“純藝術”。所以,我們就面臨著兩方面的任務:一方面,應該糾正一概不承認建筑是一種藝術,或只承認所有建筑只具有形式美意義上的“美觀”屬性,否定建筑的文化價值、忽視各國各民族文化特性的傾向;
另一方面,也必須反對片面強調其藝術性,違反建筑本性,將“建筑”整體即當作為一種“純藝術”來看待。有的人走得更遠,向往于以張揚自我為標的的某些先鋒派藝術家,同樣否定建筑藝術的民族文化特性。葉先生的主張就屬于后者且走得更遠者。葉先生說:“建筑是一門藝術,而藝術是需要想像的。有為的建筑師都應該把建筑設計視為藝術創作過程。
”這句話,若是把“藝術”定義為“廣義的”,似乎一般地可以認同,但葉先生卻非常缺乏這種分析,語意含混,結合葉先生指責中國建筑師“始終沒有擺脫‘匠人’的地位,作為工程師或藝術家而進行自由的藝術想像或創作”及其他論述,顯然,葉先生是把“建筑”本體或整體,與其他“純藝術”等同起來了。
建筑顯然具有“藝術性”,所謂“建筑藝術”指的就正是和只是建筑的“藝術性”,單純就其而言,與繪畫、雕塑、音樂、舞蹈等純藝術的“藝術性”相較,有時并不在其下,甚至還可能超過且不可替代。但“建筑”這個事物的“整體”,除了極個別者如紀念碑、紀念塔、凱旋門等幾乎就可以認為是如同雕塑般的純藝術以外,仍都具有物質與精神的雙重性,不能與其他純藝術作品混同。后者的創作自由度相對而言相當寬松,有時幾乎是無限的,基本上屬于一種個人行為,誰也管不著。
只是小偷說他的行為屬于“行為藝術”,那可就不行了。本人聽說中國最著名的一個行為藝術作品是《上吊》,藝術家的遺囑聲明他不是自殺,而是為完成一件行為藝術“作品”。雖屬個人行為,法律也拿他沒轍兒,至少也給他的家人帶來了傷害。建筑可不能這樣,無論如何,仍是以物質功能為其主要追求的,以物質條件為其前提的,離不開“雙重性”的規定。
由于建筑的極強的公眾性,建筑的設計和建造,也不可能是個人行為,即便其產權屬于私人。畢爾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館的設計者蓋里在1978年設計的有如垃圾堆的自宅,即便在特別強調個人自由的美國,也不斷引起了社區的抗議。所以,就建筑的本性而言,必然受到諸多因素的極大制約。
葉先生要求建筑師“擺脫‘匠人’地位”而隨著自己的性子進行“自由的藝術想像或創作”,對不起,不論就建筑師的職業良心而言,還是就業主的要求、經濟與工程技術條件的限制和建筑法規的執行來說,都是辦不到的。葉先生所貶稱的“匠人”,對于負責任的建筑師來說,卻正是其職業的驕傲。所以,林洙先生回憶梁思成先生的書就名為《大匠的困惑》,清華大學建筑學院紀念建院六十周年的紀念冊也署曰《匠人營國》,張良皋先生的建筑理論著作也題曰《匠學七說》,就正顯現了這一點。
葉先生說“從統治者的意向來看,從來都是強調功能而忽視藝術,重‘善’輕‘美’的傾向對于建筑的發展卻不是好事”。估不論葉先生所說是否事實,真、善、美的有機統一,卻正是建筑師非常值得追求的境界,如果能夠完美地達到這一點,正是大好之事,怎么就“卻不是好事”了?
建筑的使用功能,簡言之就是安全與舒適,屬于物質性的“善”。但實際的安全與舒適往往并不能使人們產生足夠的“安全感”與“舒適感”,而這兩種“感”卻已步入于精神性的“廣義美”的范疇了。這時,建筑師就要想盡一切辦法,在嚴格的物質性制約下,發揮自己的藝術匠心,使“善”與“美”統一起來。
這其實是建筑師必須具備的起碼的基本功,怎么能被一筆抹殺并受到指責呢?當然,這還只是對建筑藝術的較低要求,其較高的層次是運用諸如主從、比例、尺度、對稱、均衡、對比、對位、節奏、韻律、虛實、明暗、質感、色彩、光影和裝飾等“形式美法則”,對建筑進行的一種純形式的加工,造成既多樣又統一的完美構圖,即“美觀”或“好看”,使人產生美的愉悅。
多數建筑做到上述兩點也就夠了,但對某些建筑而言,還有品位更高的藝術要求,離物質性因素更遠,已屬于狹義的“真正的藝術”即“純藝術”的行列,其要義不止于悅目,而更重于賞心,富于表情和感染力,以陶冶和震撼人的心靈,其價值甚至并不在其他純藝術之下甚而超過。
然而,對上述三個層級的建筑藝術追求,都不足以成為否定建筑功能的理由。現代主義建筑四位大師之一的密斯就說過:“建筑藝術本質上是植根在實用基礎上的,但它越過了不同的價值層次,到達精神王國,進入理性王國,純藝術的王國”。雖然本人對密斯的作品尤其是其晚期的,也有一點看法,但密斯的這句話,既沒有否定“實用”和“理性”,又認識到高層級的“建筑藝術”的“純藝術”價值,值得我們深切體會。上述五部委的文件也明確批評了有些建筑“片面追求外形,忽視使用功能、內在品質與經濟合理等內涵要求”的傾向,規定,“方案設計的評選首先要考慮建筑使用功能等建筑內涵”。
至于葉先生提出的另一些觀點,諸如“反傳統是藝術革新的推進器”、“藝術貴在原創,而原創都是一次性的”、“美是不可重復的”、“想要一件成功作品的誕生,就必須容忍上百件平庸作品的出現”,以及葉先生所列中國人不如西方人的諸多判斷,還有有關建筑美的諸多定位,建議大家都慎作思考,限于篇幅,這里就不擬多談了,只想再次提出五部委的文件以供思考。文件也批評了某些建筑“忽視城市地方特色和歷史文化,忽視與自然環境的協調”;
重申建筑藝術應該“弘揚歷史文化,反映時代特征”、“重視保護和體現城市的歷史文化、風貌特色”,“要考慮建筑外觀與傳統文化及周邊環境的整體和諧”,都是建筑師應該認真體會和執行的。不管怎樣,我們還是要感謝葉先生對于建筑問題一向的關心與善意。他的某些論斷也還是可取的,有些仍具參考價值。建筑師們要創造出無愧于古人也無愧于時代、可以自豪立足于世界的作品,除了建筑界自身的努力,文化界、藝術界、評論界以及廣大公眾的更多關注,也是必不可少的前提。作者:文化部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建筑藝術研究所前所長①葉廷芳:中國傳統建筑的文化反思及展望,光明日報2006年9月7日②車爾尼雪夫斯基:生活與美學,周揚譯③劉驍純:雕塑型建筑與未來的藝術女神——從蓋瑞說開去,建筑意總第三期,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04④王寅:賀蘭山房——失敗的越界,廣州,南方周末,2004年8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