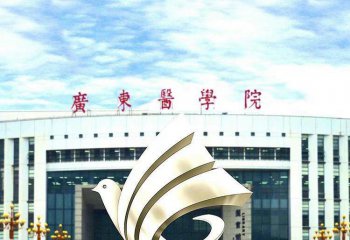在1990年代初,當代藝術醞釀的一個主要改變是,從普遍主義的語言理想退回到中國體系的形式母體。當然,這也不應該被簡單理解為追求形式上的身份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它也可被視為對于語言的主體性和自我載體的強調(diào)。王廣義較早開始學習安迪·沃霍爾的波普藝術的方法,即對于商品和明星的現(xiàn)成形象的使用,他將這一方法用于對“文革”宣傳畫的圖像改造。

這一做法在前蘇聯(lián)的波普藝術中也被使用過。1990年代初,將革命宣傳畫央美袖形象和其他現(xiàn)成圖像的波普化改造一度成為一個現(xiàn)象,像李山、余有涵、周鐵海等人,這些作品主要是將嚴肅和莊嚴的政治圖像轉(zhuǎn)化成時尚插圖的色彩風格,或者將這些圖像用花布圖案和數(shù)字符號進行拼貼,或者采用舊報紙的涂鴉藝術的形式。到1990年代中期,劉大鴻、王興偉等人實際上推進了繪畫圖像的后現(xiàn)代實驗。劉大鴻的主要語言實踐都集中在圖像現(xiàn)成元素的重組,圖像元素打破時間和空間后,實際上“再文本化”。篡改經(jīng)典的現(xiàn)成圖像后來也成為觀念攝影的一個主要方法。

除了繪畫,隋建國、于凡、張培力、薛松等人在雕塑、裝置、綜合材料和Video等媒介上也進行了類似的改造。劉大鴻和隋建國實際上開始了一個新階段,進入到一種對于形象和政治語境的現(xiàn)代性解讀層次,藝術實踐也側(cè)重于對于現(xiàn)代性的視覺載體和實現(xiàn)形式的尋求。張曉剛從1990年代前期開始關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的家庭合影,他的繪畫圖像使一種個人在大時代的變遷中產(chǎn)生的人性和日常性特征得到一種普遍意義的強調(diào)。

到1990年代中后期,越來越多的繪畫對政治攝影的圖像以及主題發(fā)生興趣,攝影圖像向繪畫圖像的轉(zhuǎn)化,這也由于1990年代后期德國畫家里希特對中國繪畫的影響。除了繪畫向攝影圖像的學習,在很大程度上,還表現(xiàn)為對于攝影的現(xiàn)成圖像的后現(xiàn)代主題和形式的改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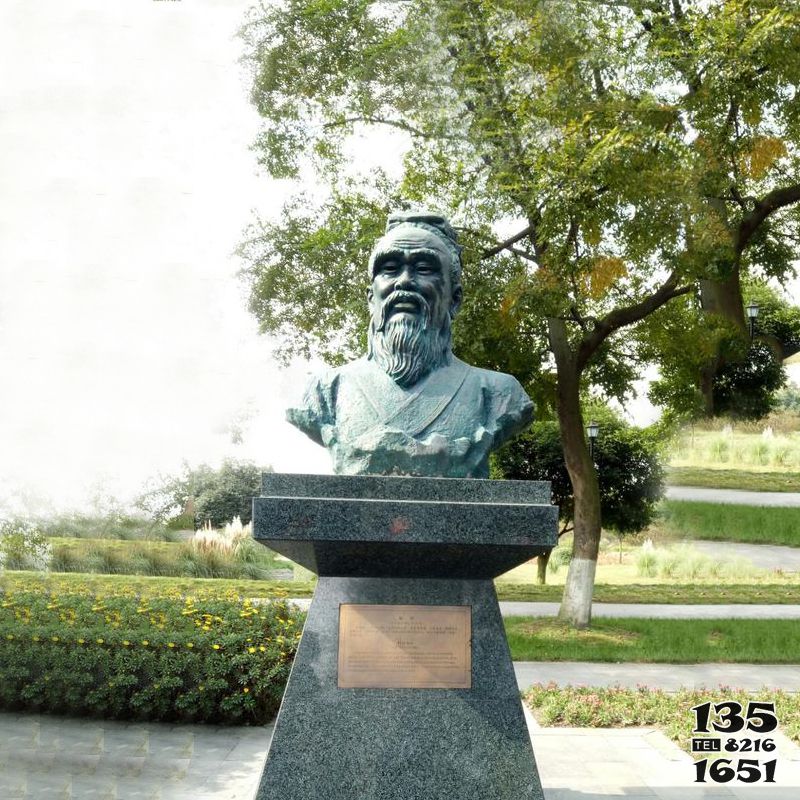
1990年代末以后,實際上已經(jīng)開始完全脫離對于現(xiàn)實和現(xiàn)代性的集體語言場,而是回歸一種個人的內(nèi)心對話。比如70后一代對于出生以前時代的隔代想象,以及上一代對于政治的宿命表現(xiàn),這還包括瞿廣慈、何杰、歐陽春等人。對于傳統(tǒng)視覺形式的語言改造,也是1990年代藝術重要的語言實踐。

1970年代以后的國際后現(xiàn)代主義,允許對于經(jīng)典圖像和歷史元素可以進行篡改和拼貼方式的現(xiàn)成形象的使用,正因為看中這一點,中國當代藝術將其看作重新與傳統(tǒng)視覺體系建立聯(lián)系的一個最直接有用的途徑。在某種意義上,對于傳統(tǒng)視覺形式的使用,母體和方法存在著一種極大的錯位,在對傳統(tǒng)視覺形式的語言改造中,1990年代以來的實踐幾乎在主題和形式上都已經(jīng)中國化,但不可否認的是,在這一場語言的金蟬脫殼中,所使用的基本方法是后現(xiàn)代方法。
作為尋找新一代人對于國家和個人變化的表現(xiàn)方式,如何擺脫西方藝術的語言軀殼,找到中國藝術自己的語言形式,這是中國藝術開始尋求真正意義的語言突破的一個開始。但事實上,使用的改造方法又是西方式的。但這一藝術現(xiàn)象在1990年代以來的實踐,已經(jīng)將中國當代藝術的語言實踐逼到了最后的關口,這一階段的意義也許在于,它可以為學習和借用西方藝術這一百年畫上最后的句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