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紀初以來,隨著西畫東漸的推進,中國水墨藝術開始進入了現(xiàn)代轉型的階段。出現(xiàn)了以徐悲鴻為代表的寫實水墨藝術的探索,以林風眠為代表的現(xiàn)代水墨藝術的探索。這兩類探索都未偏離傳統(tǒng)的規(guī)范,只是將西方藝術中的寫實和表現(xiàn)兩種方式嫁接到水墨藝術中來。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來,由于受西方現(xiàn)代、后現(xiàn)代藝術的啟示,中國水墨藝術加快了現(xiàn)代轉型的步伐,讓水墨進入現(xiàn)代一度成為了藝術家們共同堅持的理念,一批批水墨藝術家在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繼承與創(chuàng)新的焦慮中探索著將水墨畫轉換到現(xiàn)代的方法與途徑。

于是,出現(xiàn)了表現(xiàn)性水墨、新文人畫、實驗水墨、都市水墨、水墨裝置、設計水墨、觀念水墨等諸多新水墨藝術類型,這些新水墨藝術實質上也是中國社會文化現(xiàn)代轉型在藝術領域里的一種反映。而到了20世紀90年代,一些現(xiàn)代水墨藝術家相繼在一些國際性展事中嶄露頭角,然而這種交流與對話還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西方知識性話語的強權,中國藝術家實際參與的程度及其邊緣地位還很明顯。因此從1993年以后,許多現(xiàn)代水墨藝術家開始反思面對西方的話語強權,怎樣使水墨在進入現(xiàn)代的同時凸顯出中國的文化身份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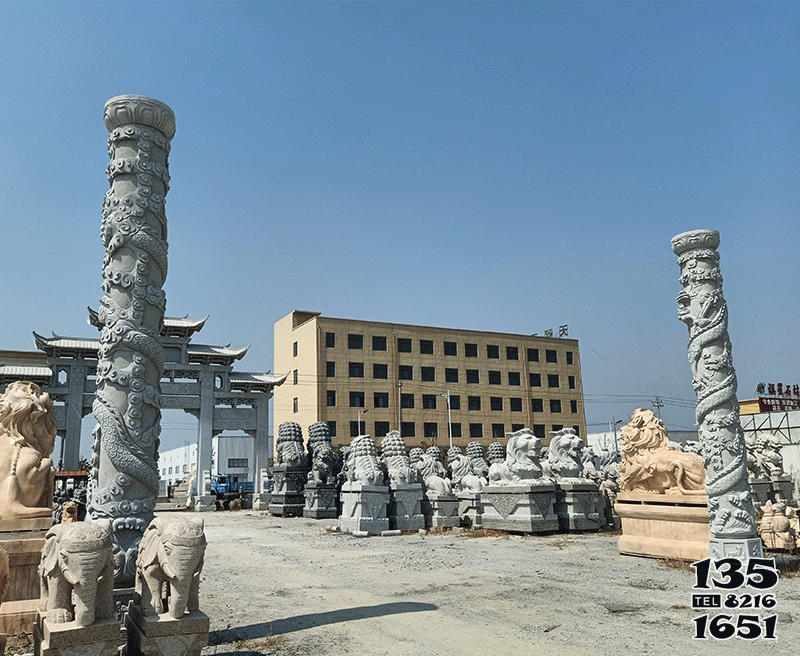
于是,中國水墨藝術現(xiàn)代轉型歷程中的兩難命題出現(xiàn)了。藝術批評家楊小彥認為:“水墨的現(xiàn)代轉換,關鍵在于解決兩難的處境,既要保留作為中國身份的水墨的自我形象,又要把這種傳統(tǒng)樣式插入到當代社會中,尋求與當代社會協(xié)調的交接點。使其不至于成為現(xiàn)代文化中的‘他者’或‘缺席者’。”一方面要將水墨導入現(xiàn)代性因素,使水墨由傳統(tǒng)進入現(xiàn)代,成為當代社會文化的藝術表征;另一方面又要凸顯出水墨的中國文化身份,使水墨在具有現(xiàn)代特征的同時,面對世界當代藝術獲得身份的確認,彰顯出水墨的現(xiàn)代形象和東方形象。

中國現(xiàn)代水墨藝術一開始是以借鑒西方現(xiàn)代、后現(xiàn)代藝術而偏離傳統(tǒng)規(guī)范的,其很難從相對比較完善的西方現(xiàn)代、后現(xiàn)代藝術體系中體現(xiàn)出原創(chuàng)性。而保留中國的文化身份又容易讓人將其與傳統(tǒng)水墨發(fā)生聯(lián)想,從而以傳統(tǒng)的思維對其進行評價。所以,擺在現(xiàn)代水墨藝術家面前的問題是:怎樣在塑造水墨藝術的現(xiàn)代形象的同時,彰顯水墨藝術的東方形象。如何解決這一兩難命題也成為了一個持續(xù)至今的問題。進入21世紀以來,現(xiàn)代水墨藝術界也出現(xiàn)了一些試圖突破這一兩難命題的水墨性實驗。

一些藝術家主張回到本土文化中去挖掘能與西方對抗的民族資源,一些藝術家則徹底沖出了水墨的材質邊界,但結果并未真正解決水墨藝術現(xiàn)代轉型中的兩難命題。究其原因在于,沒有從人類的高度來審視水墨的當代性問題。因為,不論是挖掘民族資源,還是徹底丟棄水墨材質,都還是處在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本土與西方的夾縫中,甚至很多藝術家眼中的本土化其實不過是一種狹隘的民族主義,認為越是在全球化的今天,越要強調民族性和差異化。

似乎全球化就意味著民族性、差異化的消失。其實不然,關鍵的問題在于水墨藝術如何參與到人類當代藝術的現(xiàn)代建構中去。民族是一個大的概念,但人類是一個更大的概念。民族性、差異化給藝術帶來了多樣性,但在跨文化交流與傳播中,民族性、差異化同時也制造了各民族文化藝術之間相互的誤讀。這仿佛像是“巴別塔的殘石”,困擾著文化的交流與傳播。誤讀的根源在于:一種文化總是從自身的角度出發(fā)去審視他者,這也成為了中國當代藝術建構中必須面對的問題。
而島子近年來的“圣水墨”藝術實驗,讓我們看到了一種對兩難命題進行突破的水墨藝術轉型實驗,看到了一種從人類的高度來審視水墨藝術的當代性問題的思考。基督教雖然起源于西方,但隨著其向世界各國的傳播,今天的基督教已經跨越了國家、民族的界限,成為了一種世界性的宗教,她已經不僅僅只屬于西方了,而是屬于全人類。
島子的“圣水墨”藝術正是從創(chuàng)造屬于全人類的當代藝術的高度出發(fā)來展開水墨性實驗的。所以,我們很難用東方或是西方這樣一些概念來概括他的“圣水墨”藝術,她既不是東方的,也不是西方的,而是像基督教一樣,屬于全人類。
可以說,“圣水墨”藝術突破了所謂自我/他者、本土/世界、東方/西方、中心/邊緣、傳統(tǒng)/現(xiàn)代等等這樣一些二元對立話語,也突破了一直以來困擾著水墨藝術的所謂兩難命題。在“圣水墨”藝術中,二元對立的話語已被轉化、消融,沒有東方、沒有西方,沒有對立、也沒有文化上的誤讀,有的只是基督的愛與包容。
之所以站在這樣的高度,選擇中國的水墨與基督教藝術相結合的方式來進行突破,也源于島子長期以來對中國實驗水墨藝術和中國當代藝術問題的思考、研究及實踐,也是對所謂民族主義的理性審視的結果。民族的不論有多好,如果不積極地參與到世界當代文化的建構中,而是在本民族內部堅守,那么,相反會在全球化的進程中失去民族性。強調民族特色、強調民族差異化,在今天看來實質上就是一種“封閉的堅守”,越是堅守就越沒有話語權,就越不可能獲得真正的身份確認。
民族文化的發(fā)展問題其關鍵在于要積極地參與到世界當代文化的建構中,成為世界當代文化地一部分而為人類所共享。這樣,文化就成了全人類的文明,而不是只屬于某個單一民族的文化。基督教文化不正是這樣做到的嗎?所以,島子的“圣水墨”藝術不是對民族性的堅守,他是越過“國家”、“民族”這樣一些狹隘的觀念來思考藝術問題的當代藝術家,他的實驗目的是使水墨藝術能突破兩難命題而參與到人類當代藝術的建構中去,創(chuàng)造一種為全人類所共享的中國當代藝術形式——“圣水墨”。
一直以來,中國的一些現(xiàn)代水墨藝術家總是在圖式上進行一些探索和實驗,將西方現(xiàn)代藝術的圖式轉化到水墨中,但圖式的新異并不能掩蓋其思想的蒼白,盡管可以將老莊學說、魏晉玄學、禪宗思想納入到水墨的當代實驗中,去賦予作品以意義,以此來對抗西方當代藝術,但這樣的意義也依然是局限的、牽強的,在中國都難以被解讀,拿到西方去又作何解讀?又怎么去和西方當代藝術對抗呢?
島子向來主張,藝術要承載意義,并且,所承載的意義要具有藝術史和思想史的高度。老莊學說、魏晉玄學、禪宗思想等優(yōu)秀的傳統(tǒng)資源也并非不可吸取,關鍵問題在于怎樣將其轉化為現(xiàn)代的資源去賦予作品以意義。而島子的“圣水墨”藝術實驗所選擇的是一種水墨與基督教精神相結合的方式,這也決定了其作品對基督教精神和意義的承載。縱觀其“圣水墨”實驗,又可分為三種主要探索形式。
首先是基督教精神與中國藝術精神的結合,在他2008年創(chuàng)作的作品《苦竹》中,我們既看到了禪宗思想的現(xiàn)代顯現(xiàn),又看到了對基督教精神的書寫。他將中國傳統(tǒng)文化資源中具有象征意義的竹子構成基督教的十字架,這是中國化了的十字架。梅、蘭、竹、菊、石在中國傳統(tǒng)藝術中具有象征意義,被稱為“君子”,竹子是氣節(jié)的象征,在《苦竹》中,竹子是知識分子性的象征,雖然它書寫著苦難,但它發(fā)著芽,預示著生命的生機。
另外,用竹子來構成十字架,也是對基督教的世界性的反映,她的福音傳播到哪里,就轉化到哪里的文化中,不是和哪里的文化去對抗,而是傳播著愛和寬容,生長著,發(fā)著芽…在三聯(lián)《殉道圖》中,他讓發(fā)著芽的十字架從沉重的石頭縫里長出,苦澀中又帶有幾分希望,預示著一種堅韌的精神,雖然承受苦難,但也播撒著希望。
從構成上來看,在高達3米多的作品《苦竹》中,島子用濃重的墨色在畫面的正中書寫了一個十字架,視覺上充滿了張力,實質上這樣的構成方式很難,因為十字架分割出來的四塊空白很容易產生視覺上的過度均衡感,但島子通過竹節(jié)本身的變化和發(fā)出的嫩芽沖破了這種過度均衡感,使四塊空白在形狀上、面積上有了豐富的變化。
在高達4米多的三聯(lián)作品《殉道圖》中,整體上,他將厚重的墨色安排在左下方,獲得一種視覺上的穩(wěn)定感,用十字架和竹子來劃分右上方的空間,輕重適當,乍一看有中國傳統(tǒng)繪畫的構成趣味,而細細看來,其點線面的書寫及呈現(xiàn)的各種幾何形狀的對比,又有西方現(xiàn)代藝術強調表現(xiàn)與視覺張力的味道。
島子“圣水墨”藝術的第二種探索方式是采用抽象或表現(xiàn)主義的手法,生動的書寫圣經故事。在作品《靈語》系列中,他以符號化的手法轉化了《最后的晚餐》的經典圖像,基督本人位于畫面的正中,兩旁聚集著十二個門徒,雖然沒有五官,但其生動的動態(tài)仿佛使他們都具有了表情。畫面通過潑灑的水墨形成了衍射式的構成,再加上人物疏密的處理,使觀看者的視線很自然的朝向了基督本人,以抽象的方式生動地表現(xiàn)出《最后的晚餐》的故事情節(jié),非常到位地展現(xiàn)了十二個門徒在聽到基督說:“你們中間有一個人出賣了我”時的瞬間騷動的情節(jié)。
在基督形象的外圍用稍淡的混合金粉的墨色畫了一個弧形的圈,形成了具有光暈的效果,減弱了基督形象的勾勒痕跡,以急速的書寫性突出了十二個門徒的不同神態(tài),讓我們仿佛看到了十二個門徒在聽到那一震驚消息時的騷動的表情。在作品《圣靈降臨贊美詩》中,島子同樣是采用書寫性的手法來表現(xiàn)象征圣靈的鴿子,鴿子的造型是抽象的,宛若閃閃發(fā)光的火焰,富有節(jié)奏的線條表現(xiàn)出神奇鴿子自上而下飛臨時的運動感。縱觀島子的“圣水墨”藝術,我們發(fā)現(xiàn)他的這種轉型實驗是具有神學思想含量的,以抽象或表現(xiàn)的手法將水墨與基督教進行結合的探索,在視覺上給人一種陌生化的原創(chuàng)性,翻遍藝術史也難以找到這樣的圖式。
另外,從中國水墨藝術發(fā)展史來看,創(chuàng)新一直都是藝術的題中之意,創(chuàng)新是對前在藝術形式提出的質疑,如趙孟頫針對南宋院體山水的匠氣而提出了“書畫同源”;石濤針對自董其昌以來延續(xù)到清初四王的山水陋習提出了“筆墨當隨時代”;懷著救國救亡思想的徐悲鴻提出“中國畫改良論”;林風眠針對中西繪畫各自的優(yōu)勢提出了“中西調和”;龐薰琹、倪貽德組織的決瀾社針對模仿論發(fā)表了“現(xiàn)代主義藝術宣言”;吳冠中針對藝術為政治服務的文革話語提出了“形式美”;
進入20世紀80年代后,李小山提出了“窮途末路論”…而島子的“圣水墨”是“為人類而藝術”的觀念之結晶,是針對中國現(xiàn)代水墨藝術界兩難的悖論性命題而進行的轉型實驗,是在中國現(xiàn)代水墨藝術進退兩難的情境下閃出的一道“靈光”,從他的作品中我們看到了中國水墨藝術進入世界當代藝術格局的可能性。盡管在清代和民國時期的中國基督教藝術中有采用水墨來畫圣像的作品,但在表現(xiàn)手法上多為兼工帶寫的小寫意作品,例如1930年代,北平輔仁大學藝術系陳路加、陸鴻年、王肅達、陳志華諸教授皆專心致志于中國傳統(tǒng)繪畫藝術去表現(xiàn)天主教信仰的意境,在教會中留有許多傳世名作。
而采用抽象或表現(xiàn)主義手法進行創(chuàng)作的,在島子的“圣水墨”藝術之前未能找到。所以,在基督教藝術史中,這樣的范式為島子先生首創(chuàng),其精神價值在于,以本土的視覺藝術形式與現(xiàn)代漢語神學建構起共生的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