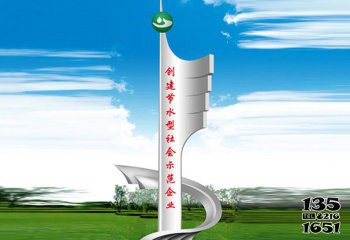不知是偶合抑是別的因緣,一種畫體的形成往往在時代甚為動蕩之后。在中國圖畫史上,山水和花鳥——這兩種幾乎可以代表中國繪畫的制作——都使我們非常容易意識到它的發達是如此。漢代有400余年的安定,經過三國兩晉而有山水畫;隋代結束了一篇濫賬,接著唐代安定了一個長時期,安史之亂,把唐代虧損了,花鳥畫即正式成立于這個時期。迨僖宗幸蜀,許多文化人跟隨著到了四川,這一移動,蜀道固刺激了山水畫的發達,同時以滕昌、刁光胤之入蜀,不久——五代的后蜀——以花盛馳名的成都,便產生了花鳥的大家黃筌父子,孔嵩及丘文播兄弟,他們俱是受著刁光胤的指揮。

尤以黃氏,所謂能“損益刁格,遂超師藝”,在花鳥畫,不但擴展了題材的領域,并且奠定了一種特殊的樣式,這便是后世“鉤勒花鳥”——即先鉤勒,后敷色彩,最初的孕成。那時候,畫家的中心地點,除成都外,尚有南京。南京自李升并楚吳閩三國而后,和山水一樣,江南美麗的大自然陶冶了一位足與黃筌頡頏的大家,叫做徐熙,創立所謂“意不在似”的畫法——即不加鉤勒的沒骨體。

從地域言,他知道黃筌雖同出于長江流域,然實際黃筌是承續著黃河流域的旨趣。這兩種形式恰如山水的金碧和水墨一樣,構成的基本元素是絕對不同的。畫面上所表現的情感也自不同,所以史家有“黃家富貴,徐氏野逸”的評語。這兩條材料、技法、樣式各各不同的路線,大體可以說一直到今天都還支配著整個的花鳥畫。在宋代,支持鉤勒畫法的有畫院,但在野的畫家則多采徐氏的沒骨,雖后來也有折衷派如“畫花點葉”之類,從縱的系統看來,還是“不入于楊,則入于墨”的情勢。

花鳥的演進及其變化,技法和樣式的范圍,固無疑地決定了一切,然而時代總是最高的權威者,南宋以后,也隨著繪畫的各部門相當地變了質,于是本從寫生而來的東西,就不免和山水一樣更視形似如無物了。最有名的故事,如蘇東坡、倪云林的畫竹,鄭所南的畫蘭,石濤和尚的畫梅,把蕭蕭幽靜勁峭的描寫,使它在道德上添加了濃厚的擔負,這原是無可厚非而且值得珍重的,不過自此時期起,所謂性靈的發揮,暴露了不可掩蔽的弱點,好像鉤勒是打倒了,以野逸自悅的沒骨折枝,也中了某類型的毒,明清以后陳陳相因,不是四君子,便是三友。

當這時候的山水,固藩籬日厚,閉庾了不少畫家,但花鳥又何嘗不如此。花鳥畫這樣的沉淪,不知何故,似乎并沒有如何被人注意,不像關心山水畫之多,我想這或是明清之際,白陽、板橋、冬心、八大諸名賢特別努力的原由。惲南田本致力于“畫花點葉”的,而世人無不稱道他的山水;以功夫學力天才人品如南田者,尚難邀賞音,可見曾成為中國花鳥畫主干的鉤勒樣式,是怎樣的衰歇,怎樣的不值錢自近數十年來,因為社會、經濟、思想,乃至生活上的種種變遷,藝術上顯然也在趕緊改頭換面,使能與商品市場相適應,不但要科學化,而且要標準化,在這種趨勢之下,所謂“美”——一種崇高偉大、精神充沛、足以感人的美就完全被美國印的法幣所替代,我們看不到謹嚴精妙的東西了。

同時我們頗以為死去的若干畫家,往往經年累月經營一幅畫的行為最笨不過,最無出息!花鳥畫家如金冬心,總算是一位大量生產的人,乾隆二十七年他忽然到漢口去玩,誰知用完了錢,于是在旅館里就結束了他寶貴的業績。市場一紅火,藝術就折腰。
傅抱石先生60多年前的這篇舊文似乎說的是今天的事兒,他在文中指出:“藝術上顯然也在趕緊改頭換面,使能與商品市場相適應,不但要科學化,而且要標準化”、“同時我們頗以為死去的若干畫家,往往經年累月經營一幅畫的行為最笨不過,最無出息!
”。藝術市場紅火是好事兒,藝術家過上好日子是應該的,可是,為什么日子一紅火,藝術就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