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時間上來說,“理性之潮”最早發生于“北方藝術群體”,其建立時間是1984年9月15日,其次發生在85年7月浙江美術學院畢業生展中,再次是于1985年10月開幕,作為《江蘇青年藝術周》一部分的《大型現代藝術展》。除去這三部分之外,其余還有數十個展覽和幾個群體都被《中國當代藝術史1985——1986》的作者們劃分在“理性之潮”范疇之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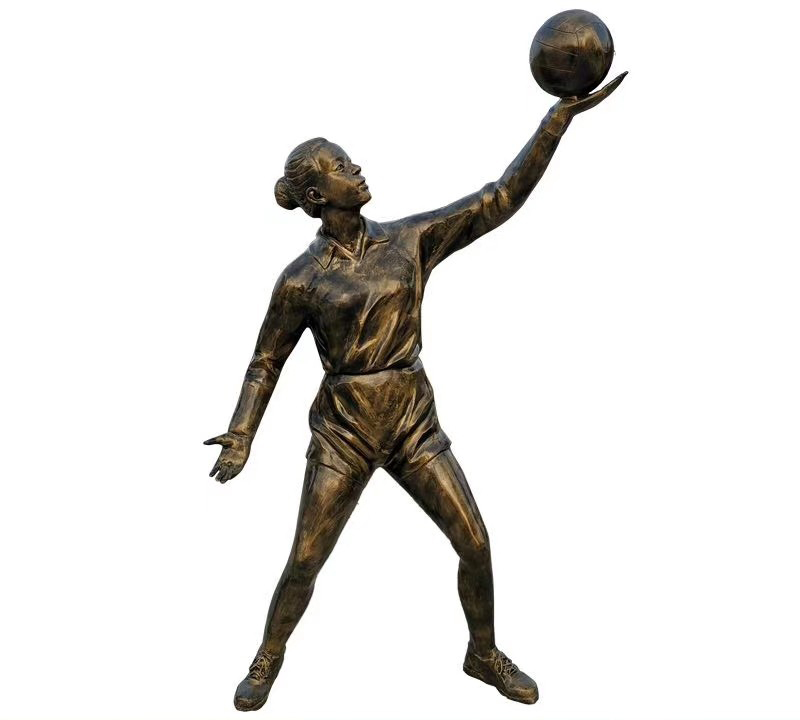
但是本文的目的并非要重新站到《當代藝術史》作者的角度上,再度總結“理性之潮”的風格特點,而是把“理性之潮”作為一個事件,研究它所發生的過程和原因。八五美術運動從本質上來說并非某些大師的運動,而是由全國各地自發的美術組織和藝術家組成的帶有啟蒙性的美術運動。

“理性之潮”同樣也是這樣,它不是一個有預謀的“起義”,而是自發話語的無意識匯集。但是,如果我們現在還將“理性之潮”作為一個自發“起義”來思考問題,就不可避免地做一些重復工作,所以,我們不妨換一個角度思考問題,即探討“理性之潮”中的“理性繪畫”概念是怎樣被接受的?我們要回答這個問題,僅知道群體出現時間遠遠不夠,因為這涉及到一個更重要概念,即話語。任何一個群體都不能孤立存在,如果“理性之潮”一直是一個自發的運動,那么現在也不會出現諸如“理性之潮”與“理性繪畫”之類的概念,而只有“北方藝術群體”、“池社”、“紅色旅”等各個團體和展覽的名稱而已。

因此,“理性繪畫”的概念必定是在一定的話語驅動之下產生了運動,并通過特定渠道進行了傳播。因此,我們不得不指出“理性之潮”的話語中心——《美術》雜志及其與之相關的話語持有者,也就是說,潛在的“理性繪畫”概念在沒有接觸到北京《美術》雜志和《中國美術報》時,幾乎處于靜止狀態。

“北方藝術群體”雖然成立于1984年,但是,因為“此時,任戩考回魯美讀研究生,而舒群留在長春工作。哈爾濱只有王廣義一人在組織活動。由于‘群體’其它成員的消極情緒及勾心斗角的瑣事的干擾,此間的‘群體’實際上是名存實亡”。舒群所謂的“此時”應該是指1984年9月份,這也是任戩研究生入學的時間。直到1985年11月,“北方藝術群體”的影響力也沒有超出邊緣性區域。《美術思潮》雜志在第二期刊發了“北方群體”成立的消息,這也已經是1985年2月-3月的事情了。

在1985年4月,“北方群體”主辦的刊物《GOD》由于行政干涉沒能出版,進一步限定了它的傳播范圍。直到1985年11月份之后,我們才能看到眾多媒體對“北方藝術群體”的報道,特別是北京的《美術》雜志和《中國美術報》兩份刊物。
與“北方藝術群體”相比,浙江的“理性繪畫”幾乎于1986年才加入到北京這個核心話語圈。雖然,1985年9月20日出版的《美術》雜志第九期中,以展覽為開端介紹了浙江美術學院畢業展,但也僅僅局限在教學領域,對其中以張培力和耿建翌為代表的“理性繪畫”關注較少。南京的“理性繪畫”在1985年10月份剛剛與觀眾見面,直到11月份,丁方的作品才得以在《江蘇畫刊》1985年11期中得到發表。可見,直到1985年10月以前,“理性繪畫”三股潮流并沒有碰到一起,“符號”的運動正是發生在1985年11月。
話語權與運動的關系越來越明顯,缺少話語權的一方必須與掌握話語權的一方相互溝通,才能使自己的話語具有流通性。在80年代,中國還存在一個關鍵詞即行政權力,此時的話語權往往依附于行政權力。同樣,藝術的話語權也要依附于行政權力,在行政權力發生變更時,藝術話語的流通也會發生相應的變化。通過這種藝術話語權與行政權力錯綜復雜的關系,我們可以看出“理性之潮”的發展蹤跡。
我們從現有的原始資料可以看出“北方藝術群體”與《美術》雜志之間的親密關系,如在1985年底,雖然《美術》雜志沒有介紹“北方藝術群體”,但是與《美術》雜志同屬中國藝術研究院的另一份刊物《中國美術報》則在1985年第18期介紹了“北方藝術群體”,并發表了舒群的文章《北方藝術群體的精神》和王廣義的油畫《凝固的北方極地》25號以及其它“群體”成員的作品。《中國美術報》第18期印發于1985年11月23日,稿件必定是在11月23日之前就已經寄到編輯部。
想必在這之前,“北方藝術群體”已經建立了與北京核心藝術傳媒的親密關系。對于“北方藝術群體”與北京《美術》雜志的關系,下面這封信件說的更明白:昨日我到《美術》去了,見到了高名潞將你的幾篇稿子都留在他那了。名潞這個人非常好,年齡與我相近,可能略大三歲吧!
他對我們的作品和你的文章很感興趣準備在近期刊用。名潞可能過段日子會給你寫信的。我把你的詳細地址留個他了。名潞告訴我前幾日中國美協油畫藝術藝委會召開學部委員會時,他把我上次寄給他的你的幾張畫和我的“極地”等作品在油畫藝術委員會關于現代油畫發展討論會上,用幻燈在討論會上放了,我們的作品放幻燈效果非常好,引起了與會代表的關注和好評。
名潞并介紹了我門的創作思想等。今晚六點我到了陶詠白家,遇到了她,與她談的很高興。你那篇《風起云涌的群體思潮》一文,詠白說她準備給你用,并讓我轉告你不要急。這是“北方藝術群體”成員王廣義給舒群的信,落款是1986年3月6日。通過信件里的措辭:“…他把我上次寄給他的你的幾張畫和我的“極地”等作品在油畫藝術委員會關于現代油畫發展討論會上…”,我們便可以看出,這已經不是王廣義與高名潞的初次會晤,在此之前,王廣義與舒群已經去過北京,并和高名潞交流了看法。
另外,我們還可以看出王廣義對高名潞的態度:“名潞這個人非常好,年齡與我相近,可能略大三歲吧!他對我們的作品和你的文章很感興趣準備在近期刊用。”這也從一方面說明了在86年以“北方藝術群體”代表的“理性繪畫”之所以能以壓倒性的優勢占據85新潮的部份原因。此信也說明了雜志刊登稿件時,很大程度上不是依靠接受陌生投稿的手段,而是根據內部的傳遞關系。之所以將“理性之潮”的時間定在1985年11月,是因為在這個月中《江蘇畫刊》發表了丁方的《漫足黃土高原所感》一文,并用一個彩版和兩個整版刊登了其作品。
1985年11月23日引發的第18期《中國美術報》首版中,刊登了舒群的《“北方藝術群體”的精神》一文,并刊登了王廣義作品《凝固的北方極地第25號》,王海燕作品《沉默》,劉劍宏作品《水桐樹》。在上文的信中,我們可以看到,王廣義在見到高名潞的同時又見到了陶詠白,并主要談了發稿件的事。最重要的是85年18期《中國美術報》頭版的編輯就是陶詠白,因此,我們可以推斷出陶詠白在85年11月《中國美術報》發表“北方藝術群體”的文章后,兩者彼此建立了聯系。
在此之前,《美術》雜志已經在9月刊中刊登了浙江張培力等人的作品,所以,我們可以說,直到1985年11月,“理性之潮”的主要三個群體才開始共同進入傳播渠道。一般的史學研究方式只是將某一個畫派的成立時間作為此畫派的開始,但“理性之潮”作為一個群體性事件,它的開始應該考慮到多個時間。再次,我們要嚴格區分事件發生時間和事件傳播時間區別。事件發生時間非常容易確定,但是它絲毫沒有意義,就像語言的私人性一樣,它不進入公共領域,就不能產生意義,所以我們要強調歷史發展過程的事件傳播時間。
傳播時間非常復雜,它會隨上下文的變化而變化——“上下文不是給定的,而是被發現的”,并涉及到符號與話語之間的復雜關系,這是我們以后要分析的問題。那么在此,我們通過傳播媒介,通過不同話語的碰撞,可以看出,確實是從1985年11月份開始,“理性之潮”的話語才共同進入傳播領域,其雛形才開始形成。是什么時間出現的“理性繪畫”這一概念呢?
我們可以肯定,必定是在1985年11月之后。我們現在需要考察的是“理性繪畫”這一概念出現之前,其雛形是什么?我們首先不得不提及為“理性繪畫”奔走呼吁的藝術家舒群。他有兩篇重要的文章,一篇是《一個新文明的誕生》,另一篇是《關于北方文明的思考》,其后來的文章都是圍繞這兩篇文章提出的觀點而進行的寫作。我們可以把這兩篇文章看作是“北方藝術群體”的宣言之作,它們同時被置于其群體刊物《God》的最前端,可見文章本身的重要性。
1985年4月是重要的一個時間點。北方藝術群體自成立之后,卻面臨解體的危險,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舒群百般周折調入哈爾濱,開始了振興群體的工作,其中一項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創辦刊物。1985年8月30日,刊物《God》大樣出廠,其中的稿件可能在9月9日的研討會之后做過一定的修改,但是基本雛形已經建立。其中《一個新文明的誕生》并沒有涉及到太多藝術上的內容,而是后一篇文章落款為1985年6月18日的《關于北方文明的思考》一文,詳細論述了關于藝術創作中的“理念”和“北方文明”崛起的問題:我們常聽到這樣的一些見解,藝術創作僅僅是個人情感的沖動的結果。
也即是對某種萬物在感情上產生了強烈的反響,持著這種感情通過藝術的手段流露出來,這便是藝術,這便是藝術的本質。然而對于理念則認為只屬于藝術的范疇,因此在藝術創作中排斥理念的作用。進而認為理論是多余的,有害的,其實從本質上要這種排斥理念的思想同樣也是受著某種理念的支配。
魯道夫·阿思海姆在他的《藝術與視知覺》一書中這樣說道:“不僅理智干擾了直覺時會破壞各種心理的平衡,當情感壓倒了理智時也會破壞這種平衡。過分地沉溺于自我表現并不比盲目地順從規矩好多少。對自我進行毫不節制的分析固然是有害的,但拒絕認識自己為什么要創作以及怎么樣創作的原始主義行為同樣也是有害的。”我想,阿恩海姆的這段論述是以說服那些排斥理念的人。
誠然,抱著墨守成規的陳腐傳統理念是創作枯竭的根本原因,然而因此排除一切理念,甚至對本時代的時代精神以及對自身的歷史使命也不加以研討,那么無疑這種盲從的“創造”必將最后走向毫無疑義的廢品排瀉。打個比方說:從古代希臘到文藝復興好比建起一座“大廈”,而出現在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的“現代派”思潮,恰是“拆除”這個已在腐朽的大廈的過程。
因此,迪尚在《蒙娜麗莎》的美麗面孔上加上胡須的意義正在于此。無庸贅言,當我們沉思著從當代這種紛繁的“新世界”中走出之后,我們都會承認這樣一個真理:“現代派”不是完美的!畢卡索不是完美的,達里不是完美的,拋去對“現時代”的狂熱,當我們從一個更高點立足之后,我們便會看到“現代派”的高峰與之古希臘和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相比較,無異于富士山與珠穆朗瑪峰的比較。更形象些說,比起古希臘、文藝復興的大廈,“現代派”不過是一堆瓦礫。顯而易見,破壞行為比起建樹行為總要短暫很多,從古希臘到文藝復興歷時幾千年建起的藝術圣殿竟在一夜之間成了破磚爛瓦,同時又如摧毀這座大廈那樣迅速,人們很快就清理掉這一廢墟,開始了新的建設。
在整篇文章中,藝術家集中反對了創作中的情感至上主義,并批判了由這種感情沖動所引發的現代主義運動。這當然出自舒群思考的兩個緯度:第一,在藝術實踐中如何體現冷靜的創作觀念;第二,怎樣建立一個能夠概括其群體藝術實踐的概念“北方文明”。“理念”是舒群文章的關鍵詞,它不僅關系到藝術的創作,而且是其“北方文明”之所以能夠成立的基礎。在此,“理念”的對立面是“個人情感的沖動”。
舒群認為理念不僅存在于“藝術”中,同樣也存在于“藝術創作中”,因此,“理念”又同時具有了“理論”的含義。通過引用阿恩海姆的語言,他更加明確了“理念”的含義,即藝術創作中的冷靜態度,也可以說是一個藝術家在創作過程中所擁有的理性。“理念”和“個人情感的沖動”的對立并沒有結束,舒群隨即將理論的重點轉移到了文化上。他將“個人情感的沖動”與西方現代藝術的“任意揮灑的潛能”聯系在一起,并將“理念”與古代希臘與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歸為一類。
在這兩者的比較中,西方現代藝術無疑成為“一堆瓦礫”。那么,他們所謂的“北方文明”就是建立在被現代藝術毀掉的西方古典文明的廢墟之上。因此,在形而下層面上,他認為“理念”是藝術創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形而上層面上,“理念”又是“北方文明”的關鍵因素。至于后者,它明顯來源于黑格爾的美學理論——“美是理念的感性顯現”。“理念”在此包含三個要素,首先是“概念”,其次是“概念”的表現形式,最后,是兩者的統一。
如果再往后追溯,我們更能看到柏拉圖的影子。“理念”作為世界最高的核心,是萬物之始,藝術則是處于對“理念”模仿的模仿。無論是黑格爾還是柏拉圖的理論,都顯示出了“北方文明”的傾向性。在舒群后來寫的文章中,要表述的更加清楚:一九八五年七月我又在哈爾濱的朋友的介紹下看到了《凝固的北方極地》這套組畫,又一次的震動,觸及心靈的震動,荒漠的原野,暗藍色的天空,凝固了的人形再一次展現了北方那種神奇偉岸的世界,這種互不知曉的同構意味著什么呢?
此次遭遇不能不引起我的深思,在我重新翻開世界美術史的時候,我發現了文化中心北移這一重要特點,西方文化從埃及、古希臘、古羅馬、佛羅倫薩到巴黎,西方的文化中心在逐漸北移,同時在這種北移停止了的時候西方文化也就隨之消亡了。這篇寫于1985年7月之后的文章表明,在看了王廣義的《凝固的北方極地》系列作品之后,更加堅定了舒群對“北方文明”與西方古典文明的傳遞性關系。但是,在此之前的那篇《對北方文明的思考》并沒有清楚地點明“北方文明”所蘊含的“理念”的具體含義,或確切的說是沒有說明“理念”落實到畫面上應該呈現什么樣的結構。
1985年《God》雜志由于各種原因沒有能夠出版,導致應當進入傳播渠道的文章失去了應該有的傳播效應。但是,早在《God》大樣出廠之前,在1985年7月出版的《美術》雜志上,刊登了高名潞的一篇名為《近年油畫發展的流派》一文。在這篇文章中,作者用了三對相互對立的概念對70年代末到85年之間發生的藝術現象進行了初步總結,其中第二部分名為“理性主義·自然主義”。我們有必要看一下他對“理性主義”的論述:“在任何一個偉大的情感的復興之前,必須有一場理性的破壞運動”,這個破壞運動出現了。
由青年業余畫家和專業畫家組成的一些畫會,特別是“星星畫會”,為這一運動的先鋒派,過去的條條框框在他們那里要少得多,因此其要求解放的口號就徹底得多。他們的創作觀念走在了實踐的前面,“藝術是理念的感性顯現”,對于他們來說再合適不過了…他們代表著新時期中新一代的審美思潮的趨向,他們要將久被壓抑的胸中的巖漿噴發到畫面中去,他們要表現運動,表現加快了的時代步伐。
你看艾未未的《水鄉碼頭》、肖大元的《魚與網》、何寶森的《路漫漫》,那些點與線、面與體在多方向多中心地躁動著。運動就是美,世界的本質就是運動。他們的可貴之處也正在于作品中顯示的理念的沖動。他們之中的一些“靜態”的作品又似是凝固的巖漿,是熱情凝縮成的哲理和觀念。如甘少誠的《主角》、陳延生《隕》、嚴力的《對話》,我不能確切地解釋它們,也不了解作者的動機,我與他們毫無過從,但我知道這里含蘊著他們要說明的某種社會哲理。理念是情感的伴和物。按照格式塔心理學家阿恩海姆解釋,情感活動是對總的精神活動發動起來之后使神經活動達到某種“沖動程度”的體驗。
這是藝術創作的動力和支配物,這動力的來源則是“一個人有意識或無意識地意識到的全部事物和事件”,這里有理念的成分,有意識的支配,但它必須是與無意識和不能被準確地知覺和推理的東西相協同的。二者的渾然天成是藝術品偉大之所在。
由于功能主義的畫家們的意識和觀念太強了些,他們似乎還缺乏某種特定的形式,遂使其作品有些圖解之嫌。蘇珊·朗格曾說:“純粹的自我表現是不需要形式的。”表現可以隨意,而藝術形式卻不能隨機,它永遠是個別的,是不能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如果說“理念”在舒群的文章中既有理性的含義,又有概念的含義的話,那么在高名潞的文章中,術語的運用則更為準確到位,“理性”和“理念”已經有了初步區分。“理性主義”一詞,在文章中被作者用來形容以“星星畫會”為代表的強調功能主義的畫家們,用以說明他們具有的強烈自我意識和觀念性。
而“理念”則是用來說明“星星畫會”藝術家的創作方式,即創作觀念要先于實踐。高名潞明確說明了舒群文章的內在邏輯——“藝術是理念的感性顯現”。所以,“理念”在此文的含義更加明確,就是指藝術創作的概念及其實踐,那么“理性主義”則是對這種“理念”現行的創作模式的理論總結。因此我們可以說舒群更多是從一個藝術家的角度來思考自己的藝術創作及其要表達的文化內涵,而高名潞則是站在《美術》雜志編輯的角度,站在批評家的宏觀角度來對全國的藝術現象進行總結。
這篇文章的寫作上下文是“第六屆全國美展”的舉辦以及展開的相關討論。在《美術》雜志1984年12月刊上刊登了署名為“時真”的標題為《第六屆全國美展油畫研討會在沈陽舉行》的報道文章。文章首先以官方的辯證口吻提示要“充分肯定油畫的成績”,其次才提出了油畫創作中存在四大問題:1、“題材決定論”的影響依然很大,有些作品仍然是所謂的“大題材”,架子大,板著面孔,使觀眾感到疏遠。
2、有些作品重視美術的教育功能而忽視美術的審美功能。說教、說明,而不能給人以美的享受,使觀者感到乏味。3、形式風格過于單調和簡單,油畫形式的豐富性和技巧的特殊性,未能得到充分研究和發揮。4、油畫應該走出展覽館、博物館、畫院和學校,到社會上去,滿足廣大人民對油畫日益增長的需求。以上四大問題成為全國美術工作者特別是美術青年所關注的主要問題,“在畫家中似乎有‘凡是六屆美展擁護的我們就反對’這樣一種逆反心理存在”。反對第六屆美展的思想成為85年青年藝術家創作的主要動力,高名潞處于《美術》雜志這樣一個核心話語地,一定意識到了這個情況,所以在《近年油畫發展的流派》、《三個層次的比較》和《一個創作時代的終結——兼論第六屆全國美展》三篇文章中,依次總結了一個時代結束,提示了85美美術運動的合理性。
從這個上下文來看,作者大多用否定的語氣來敘述昔日的美術創作。讓我們再回到《近年來油畫發展的流派》一文中去,看一下高名潞提出“理性主義”的真正用意。高名潞通過對星星畫會的論述所引出的“理性主義”并非贊揚這種理念先行的創作模式,相反是對這種方式提出批評性意見。
他首先認為星星畫會的藝術家有兩種創作風格,一種為“動態”,另一種為“靜態”。并且這兩種形態都屬于“理念先行”的創作方式。繼而又認為這種理性主義由于過于注重藝術的功能性,從而放棄了藝術本真的一方面。也就是說,他在這篇文章中批評理性主義,主要是因為理性主義藝術家在創作過程中只有好的理念是不行的,還必須注重藝術的形式,只有形式與內容的完美融合才是理性主義的最佳狀態。如果我們回頭思考一下高名潞提出這個批評性觀點的依據,或許能夠發現一個有意思的現象。
在批評理性主義之前,他在文章中先引用了阿恩海姆的一段話,用以來證明藝術創作中理念與無意識的相互融合才是藝術創作的最佳狀態。但是,在舒群1985年6月18日寫的《關于北方文明的思考》一文中,同樣引用了阿恩海姆的話作為自己論證的基礎,但是得出來的卻是更為極端的結論——理念是藝術創作的根本,其與激情相互對立。
同樣是應用了阿恩海姆的理論,兩人卻得出了不同的結論,從表面上看,是因為他們各自引用了阿恩海姆不同的語言,但是,其實質是兩人對以“理念先行”之藝術理解上的差異。在舒群的文章中,理念在藝術創作中只有一個發展方向,就是冷靜的分析;而在高名潞的文章中,理念之于藝術創作則有兩個發展方向,即激情和冷靜的分析。因此,理性主義在產生之初就具有了兩層含義:有理念的激情和有理念的冷靜,這同時也是高名潞在1986年《85美術運動》一文中分析“理性繪畫”三種主要樣式的最初模式。
通過對兩篇文章的對比,我們就能夠知道,不管是藝術家還是理論家,在1985年11月之前都沒有提出“理性繪畫”的概念,而是提出了與這個概念最接近的“理性主義”和“理念”的概念。但是,很明顯,“理性主義”和“理念”并非處于一個敘述層面,一個出于總結性的理論敘述層面,一個出于實踐性的操作層面。所以,后來“理性繪畫”的概念應該出于“理性主義”的邏輯,而非出于“理念”的邏輯,畢竟,“理性繪畫”和“理性主義”是出于同一個敘述層面,前者相對于后者只是內涵的不斷擴充而已。
而我們應該明白的是,在高名潞寫出《近年油畫發展的流派》一文時,他并沒有關注到“北方藝術群體”成員的活動,同時,此群體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也還在創作之中,所以在論述“理性主義”時用了星星畫會的例子,而非后來典型“理性繪畫”的代表——“北方藝術群體”。舒群對“理念”概念的闡釋雖然沒有上升到理論高度,但是卻恰當地總結群體的藝術指向,明確了“北方藝術群體”對繪畫中“冷靜”風格的追求,這種風格也成為后來“理性繪畫”的主導風格。
《北方藝術群體歷史資料歷史資料》,舒群,《八五美術運動》,高名潞等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北方藝術群體歷史資料》舒群“討論會之后,理論刊物《GOD》即將成書。正值此時,來至省里各方面的壓力和國家關于出版物的通知迫使我們停刊。但是國內有關刊物相繼報導了《GOD》創刊的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