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來推一篇短文————一切都是那么祥和寧靜,一切都那么富有詩意。一只大白狗跳了出來,它搖晃著腦袋,追著自己的尾巴團團轉。嘿,多傻啊,自己能咬著自己的尾巴嗎?許是金宇太過得意忘形,大白狗竟然呲牙咧嘴的發出嗚嗚的低鳴聲,這是赤裸裸的威脅啊!金宇猛的向前踏了一步,它像一只受驚的耗子一樣縮了回去,留下一個委屈的眼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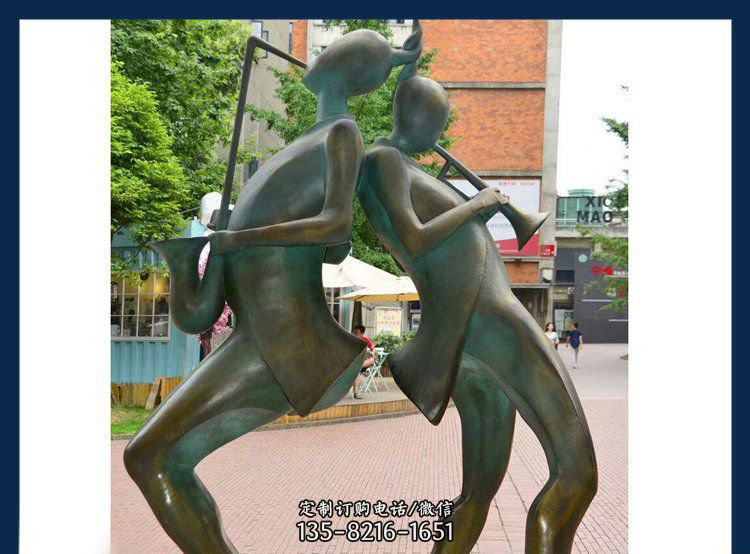
金宇才不管它,這識人性的家伙,難怪富家大戶都愿意飼養它。果然,它又湊了上來,擺出一副攻擊的姿勢。金宇懶得理它,這個畜生!突然,大白狗嗚嗚的,金宇心里猛的一跳,遭了,“汪汪汪”幾聲狗吠聲傳的極遠,金宇不懷好意的盯著這個始作俑者。大概是知道闖了禍,它趴在地上,嗚咽著。金宇不由得有些好笑,正要蹲下勸慰一下時,灌木背后傳來腳步聲。金宇挺直身體,看著來人——這是一個身著制服的中年男子,他微笑的打過招呼,恭敬的鞠了鞠躬。
哈,感情花匠把他當成主人了,花匠腳步不停,他提著自己的花剪消失在花園里。大白狗懶洋洋的吐著舌頭,渾然一副地主模樣。這個別墅里大概還沒有住進多少人來,偌大的花園再見不到別的人了。白狗悠閑慣了,它見跟著金宇并沒有零嘴可吃,一溜煙的鉆過灌木消失不見了。那搖晃的尾巴和龐大的身軀震的灌木的枝葉漱漱落下。東莞地處南方,金宇以為這里的草木盡皆蒼翠,不想滿眼綠色之下卻是一片枯黃。
哈,果真是表象啊,也不知道是人學了植物的新枝換舊葉,還是植物覆蓋了人的光鮮亮麗?金宇捏了一支枯黃的葉片,細細的打量著他的紋理。陽光下,葉片葉脈清晰可見,一抹晶白的亮色突然閃了過去,清風拂過樹梢,露出著塔尖來。冬天的灌木不免輕浮,低低的,嬌羞的潛藏著自己的丑陋。美麗的喬木自然不同凡響,坦坦蕩蕩的,叫人艷羨。
我把教堂指給接引的使者,鮮花不語,藤花卻淡淡的開放。如果東莞愿意捕捉上帝,那么吾等的內心便不在彷徨。沿江直上,他驚喜的看到一大片的莊稼地,他以為是莊稼地,綠油油的苗兒迎風招展著,但近了才發現是種不知名的花卉,幾個園林工人坐在地上撥弄著土壤,細心的把花卉移植了進去。其中一個看著像個女人的工人呆坐在那個專注的身邊,長期生活的艱難使她顯得疲憊不堪,神色已變得向老年人一樣呆滯而默然,還有一個坐在土里,小口小口的吐著煙圈…
那樣的場面,驀然讓金宇有種震撼的感覺,他直覺上總覺得哪兒見過這樣的景象,是在哪兒來著?喔,對了,是那個法國著名的晚期現實主義畫家勒帕熱,他的《垛草》代表了法國19世紀現實主義最后的輝煌。“生活原來處處是藝術啊”他輕輕的吐了口氣,白色的霧氣呵成一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