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伯樂受楚王的委托,出去尋找一匹能日行千里的寶馬。盡管歷經千辛萬難,伯樂卻始終沒能相到楚王心目中的那匹千里駿馬。某日,伯樂乘車從齊國返回楚國,看見一匹馬拉著沉重的鹽車翻越陡坡。盡管馬匹用力掙扎,膝蓋跪屈,大汗淋漓,在山坡上還是拉不上去。但伯樂一眼相中,此乃千里馬也。他立即下車,脫下隨身衣物,披在馬背上,自己暗暗抹著眼淚。說來也是奇怪,那匹馬見到伯樂之后,低頭噴氣,仰天長嘯,如同金石之聲,驚動天地。

楚王將信將疑,跨馬揚鞭,打算試試此馬。怎知喘息之間,此馬已跑出百里之外。距今5000多年前,傳說中的三皇五帝時期,中國人已經從養馬、食馬,進入了馴馬階段。在馴馬的過程中,人們逐漸為這種草食系動物找到了它們最契合人類的功用。

早在殷商時期,“馬”便在甲骨文中擁有一個獨特的形象:一匹駿馬的側面。而我們現在所能看到的甲骨文,盡數刻于龜殼或獸骨之上,主要為殷商時代王室用于占卜或祭祀時使用。因此,馬這種動物,毋庸置疑是殷商先民用于祭祀神靈或先祖時的祭品。隨著時間推移,人們在畜牧過程中,逐漸發現這種四肢健全的動物在力量和速度上有著先天的優勢。于是,中國最早對于馬的現實運用——馬車,隨即誕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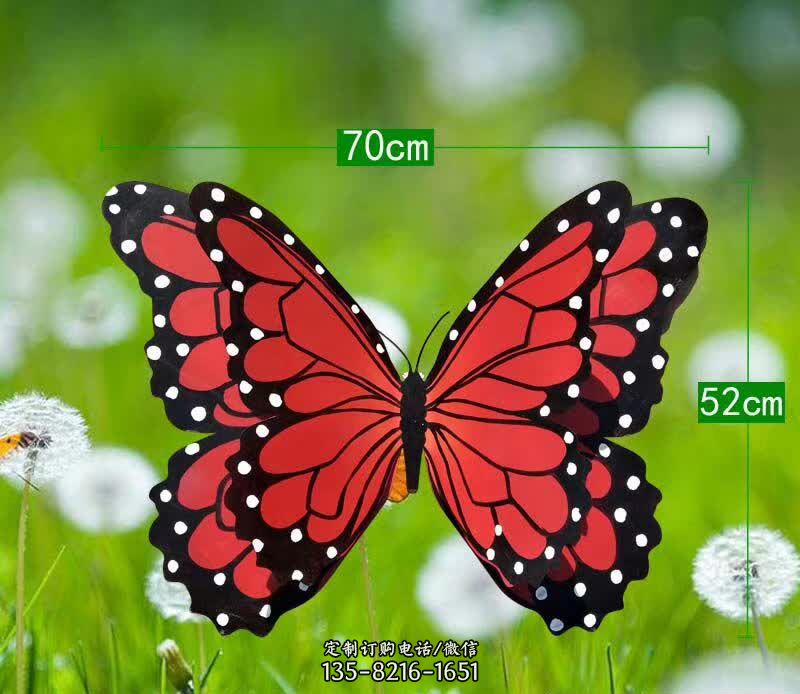
不過,據《史記》記載,中國造馬車的時代應該遠早于商代。因為早在殷商出現前的幾百年,大禹治水時,人們已可做到“陸行乘車,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輦”。盡管這四種當時的交通工具并未傳下來,但在今天河南安陽殷墟遺址上,考古學家已然發現了商代晚期制造的雙輪馬車。正如甲骨文中,另一個漢字“車”的形象,商代雙輪馬車主要由轅、衡、輿、輪、軸等部分組成,多以兩匹馬并行牽引,與之后的“天子駕六,諸侯駕五,卿駕四”的馬車不在一個等量級上。

有理由相信,先民們最早發明馬車,并不一定是為了戰爭而準備的。但馬車的出現,無疑讓靠兩條腿走路的人們,速度上獲得了極大的提升。在那個弱肉強食的時代,資源的多與少將決定著一個部落乃至一個國家的生存與發展。故而,馬車應用于實戰,只是時間問題。到了周代,宰馬祭祀、食用以獲得能量,已然不是社會的主流。但爭奪資源的權力游戲卻不斷地升級加碼。戰爭成為了爭搶資源的最直接方式,誰的速度快,意味著誰有資格主宰天下。

周朝甫一建立,在《周禮》中,就對“馬”的功用、品質等方面做出了明確的劃分。規定天下之馬可分為六種:有用于培育后代的“種馬”,用于打仗的“戎馬”,用于典禮上撐排場的“齊馬”,供日常運輸的“道馬”,打獵用的“田馬”,以及馬匹預備隊“駑馬”。在這六種類別中,馬的品質還以其身長又被細分為龍、騋、馬三等,并規定馬的數量和等級,使每一匹馬,能在周朝貴族的馬廄中物盡其用。

于是,一大批裝備更加齊全的戰車部隊得以面世,并在日后天下混戰的春秋戰國時代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姜太公封齊戰車雕塑,現藏于山東省淄博市齊文化博物館。圖源:圖蟲創意不過,正如前面所說,戰馬的特長是速度與耐力。以馬拉著車在戰場上馳騁固然威力巨大,但實際上也加重了戰馬本身的負擔,并不適用于靈活多變的戰場。

面對復雜的戰爭環境,笨重的戰車往往騰挪不及,指揮調度的機動性能太差,一旦遇到大軍團規模作戰時,除了往前沖,毫無退路。而另一方面,馬匹性喜成長于水草豐盛之地,健碩的外表下,掩藏著一顆躁動的心。中原人養馬、馴馬、食馬,以馬為工具拉車,無疑使馬本身失去了原有的天性。故而,中原的戰車再強,在性能和機動上都遠不如北方的原始野馬。

于是,戰國時期,趙武靈王啟動了“胡服騎射”的改革,徹底釋放馬匹的天性,使之成為日后戰場上與士兵共進退的“好伙伴”。中原土馬的天性,經過多代人的馴化,早已磨滅了桀驁不馴的本色。即便有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改革,以騎兵著稱的趙國最終還是敗給了秦國。

作為中國封建社會的第一個大一統王朝,秦朝的祖先最早就是養馬的。在養馬、馴馬這件事上,秦國可謂開春秋戰國風氣之先。在秦國崛起的過程中,秦人一直以馬為立國之本,對馬匹的熱愛也遠超諸國。秦朝統一天下后,中央的太仆即有為皇帝培育、管理馬匹的職責。由于周天子偏心,秦國的封地處于北方游牧民族犬戎的勢力范圍內。自分封之日起,秦人便在生存空間上與犬戎進行著抗爭。這一期間,隨著秦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犬戎的實力被大幅削弱。

在戰爭中,犬戎的良馬也源源不斷地補充至秦國軍隊之中,為秦國培育出良種戰馬作出了突出貢獻。由于犬戎的戰馬個頭較大,多為重型挽馬,比起載人騎射,它更適合拉車。因此,當秦國具備統一天下的實力時,其戰車部隊的規模甚至超越了騎兵部隊。現今世界馬種中體型最大的英國夏爾馬,當年來自犬戎的良馬與其一樣擁有粗壯的四肢圖源:圖蟲創意進入漢代,由于此前秦末漢初天下紛爭甚劇,加上北方游牧民族匈奴的崛起,中原地區百廢待興。此時,即便貴為天子,想找到一匹純色的馬來拉車都難。

為了再度振興養馬業,也為了盡早解除匈奴對中原地區的威脅,漢文帝首先頒布了“復馬令”,規定一人養馬、全家不用上戰場,鼓勵百姓養馬資助國家。由此,漢代民間養馬風氣始盛。漢文帝的“復馬令”中同時包含了一些禁令,如“盜馬者死”,并規定馬匹身高未達五尺九寸者,嚴禁出口。除了大力鼓勵民間私營養馬業,漢朝前期的皇帝們亦不放過任何一個培育良馬的機會。漢景帝在位期間,天下設有36處“牧苑”,專為皇家養馬。而漢武帝為了得到良馬,更是不惜將細君公主遠嫁、命令張騫二次出使西域,將烏孫天馬、大宛馬帶回漢朝,雜交培育良種馬匹。

經過漢代數位皇帝的共同努力,至漢武帝時,天下已然“牛馬成群,農夫以馬耕載”。隨著良種馬的興盛,大漢突騎也初具規模,并在與匈奴的戰爭中,屢戰屢勝,威震天下。祁連山腳下的山丹軍馬場,為漢武帝時期霍去病所建,目前為亞洲最大的軍馬場及我國境內最大的糧油肉生產基地。

圖源:圖蟲創意漢朝騎兵雖強,但戰斗力其實未能得到最大程度的發揮。以弓箭和弩作為主要作戰武器,需要一個更為穩定的膛線,方能精準地擊中目標。可是當時騎兵的坐騎多數只配備單邊馬鞍,更沒有馬具中常見的馬鐙,故而穩定性極差。直至東漢時期,中國的冶鐵技術進一步提升,加了軟墊子的高橋馬鞍與馬鐙才被發明出來,并運用于騎兵戰具之中。中國古代騎兵由此迎來了一波發展的小高峰。

當時,為了激發騎兵部隊的作戰優勢,各方政權都在騎兵軍事技術上花費了大力氣。東漢末年,一種新型的金屬馬鎧問世,從此騎兵胯下的戰馬也有了安全保障。所謂具裝,即重裝騎兵,由戰馬與士兵同時配上鎧甲,使之攻防兼備,在戰場上所向披靡。但這對戰馬本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可以說,戰馬的體格以及冶鐵工業的水平直接影響了重裝騎兵的戰斗力。

東漢之后,中國再次進入大分裂時代,北方游牧民族大規模南下。直到隋唐時期,中國再度回歸天下一統,具裝騎兵的優勢才真正地得到重用。當年漢武帝大量引進的烏孫天馬和大宛馬,根據考證,即今日的伊犁馬以及土庫曼斯坦國寶——阿哈爾捷金馬。這兩種馬具有步履輕盈、速度快、力量大、耐力強的優點,但皮薄毛細、頭細頸高、四肢修長的特征,也注定了它們無法扛住士兵與負甲的重量。

重新尋找一種優良的馬種,進行雜交培育變得尤為重要。所幸,隋唐時期具有游牧民族鮮卑傳統的關隴貴族對馬匹的重視也堪比漢朝。隋煬帝首先對久不納貢、且位于中原與北方游牧民族之間的高句麗政權發動進攻。在那里,他見識到了全副武裝的高句麗具裝騎兵的威力。盡管遠征的結局因隋朝被推翻而不了了之,但經過數次交鋒,互有勝負的戰績也讓中國戰馬有了一次優勝劣汰的雜交選育機會。

緊接著到了唐代,更擅長使用騎兵戰術的唐太宗李世民,以個人膽識和強盛軍威,征服了擅長育馬的突厥部落。中國再度進入一個大規模的養馬育馬時代。這一階段,唐帝國的馬種獲取渠道從過去的單向進貢、民間養馬階段,轉變成開放互市、官方育馬階段。

在唐朝境內,帝國下設牧馬監,專事放牧事宜。從唐太宗貞觀初年開始,官方就有意識以三千匹馬,從赤岸澤移往隴右一帶去放牧。可見,唐代的馬匹規模從一開始就比漢朝大得多。正如《新唐書》中記載,“方其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馬的價值在當時僅相當于一匹絹布。與此同時,中國的獸醫技術得到了快速發展。以往,歷代的獸醫以父子相傳、師徒相繼的方式進行。

進入唐代后,隨著官方對畜牧業的大力扶持,獸醫需求量劇增。故而,在官方設置的太仆寺中,有專門的獸醫為各種引進的良馬和配育出來的新馬提供健康保障。唐朝先后出現了各種經西域引進的良馬,如吐火羅馬、骨立干馬、阿拉伯馬等,滿足了唐朝全盛時期的用馬需求。由此,圍繞著“馬”展開的各種文娛活動,給中國歷史留下了一段最精彩紛呈的畫面。這些以“馬”為核心的活動,大大激發了當時工匠們的創作靈感,代表當年藝術風格的各種“寶馬”也相繼問世。隨著安史之亂的爆發,唐朝從前用于養馬的河套地區丟失,國勢由盛轉衰。

曾經熟悉的割據政治,又一次將盛唐拉入水深火熱之中。戰爭的深入,意味著國民乃至上層貴族都不再有像之前那樣的閑適時光,騎馬消遣。另一方面,馬本身就是古代軍隊戰略物資,戰爭的持續也意味著馬匹的持續損耗。茶葉含有的茶多酚有助于解油膩,對于常年以肉食為主的游牧民族來說,不失為一種生活必需品。同樣,對于唐、宋而言,良馬也是他們維持統治、繼續戰爭的保障品。

在茶馬貿易過程中,宋代官方又將茶與馬的品質價格對應掛鉤,明碼實價貿易之余,又為宋代軍馬供應把控了品質。盡管宋朝丟失了傳統的天然養馬區域,但他們并沒有放棄重新依靠自主研發來獲取良馬。兩宋時期,官方在境內多地恢復馬監。據記載,僅北宋首都開封一地,官營馬監就多達21處。

與漢代一人養馬、全家免稅不同,宋朝采取的“保甲養馬法”,是定時定量給百姓下發生產目標,完成后由官方出錢收購。正所謂“物以稀為貴”,宋朝先天馬匹匱乏,自然令民間百姓在按規定產馬之余,偷偷從事各種與馬相關的走私勾當。有鑒于此,宋朝法律規定極其嚴苛,走私良馬通通按謀反罪處理。即便是如此,宋代的良馬也僅僅夠軍事開支使用。當橫掃中世紀歐洲的蒙古騎兵南下時,宋代軍隊難有力氣抵抗。

蒙古人自行馴化了“蒙古馬”,并將其裝配在馳騁天下的蒙古騎兵部隊中。這種馬長期生存在蒙古高原,既沒有舒適的馬廄,也沒有充足的飼料。故而,蒙古馬體型短小,頭大頸短,與傳統的重型挽馬有著很大的不同。在作戰中,長期使用歐洲重型挽馬的歐洲十字軍等著名的具裝騎兵團,才會如此輕視蒙古馬這種馬界中的“矮窮銼”。
但“矮窮矬”的戰斗力一點兒也不弱。由于常年生活在野外,蒙古馬長得皮厚毛粗,四肢健壯,不僅能抵御西伯利亞的寒冬,也能一腳踢爆野外孤狼的腦袋。只要稍加馴化,蒙古騎兵依然能組建起一支戰斗力可觀的鐵騎部隊。事實也是如此,從成吉思汗開始,蒙古騎兵西進、東征、南下,不僅入主了中原,還將版圖擴展到史上最寬。
蒙古帝國進入大元時代后,仍然注重馬匹的培育與保養。據史料記載,蒙古族是我國最早掌握閹割馬匹技術的民族之一,雖然去勢有助于馴馬者更容易馴化馬匹,但被馴化的馬匹將朝著性格溫順的方向發展。在馬匹的日常保健上,元朝政府十分重視。《元史》記載,為了保障蒙古戰馬的優勢得以延續,元代官方在飼養官馬時,會在飼料中摻入鹽,使馬匹在吃完后,保持體內滲透壓,防止水分過度流失,進而也有緩解疲勞的作用。到了明代,隨著元帝國的崩塌,蒙古人退出了中原。
盡管,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最早只是個到處化緣的窮苦和尚,但在建立大明的過程中,他見識到了蒙古騎兵的強大,因而一坐上皇位就立即下令將“馬政”確立為國政。在民間,明代的養馬業首度采用了計丁、計戶、計畝的方式,對馬匹進行飼養。但與宋代那種馬養好了,官方去“摘桃子”的行為不同,明代的民間養馬更像現代農業上的“包產到戶”——雖然國家也會根據需要去民間征收馬匹,但此時的養馬戶,對“馬”這種動物已享有私有權,當“馬”這種財產出現損壞、缺失時,官方是需要照價賠償的。然而,這種養馬、育馬的方式終究敵不過持續增長的人口和不斷被兼并的土地。
據《明史》記載,萬歷年間,全國人口已達1.5億,以皖西為例,相較于明初,這里的人口已然猛增了2-3倍。加上皇室宗藩、地主豪強之類的人,在全國瘋狂兼并土地。百姓的賴以生存的農耕空間尚且難以保障,誰還有時間、精力去養馬?作為中國最后一個封建王朝——清朝,騎馬射箭本來就是滿族世代相傳的基礎生存技能,馬的運用幾乎貫穿了這個朝代最后的時光。
清代前期,為了適應與關外截然不同的生活環境,久居深宮的康熙皇帝定下規矩:“皇太子、皇子等既課以詩書,兼令嫻習騎射。”在清代統治者眼中,騎馬射箭是國之根本。為了保障良馬的正常供應,清代的馬政體系分皇家和國家兩種。除了延續前代留下的中央和地方馬政外,內務府管轄的上駟院專為皇家培育挑選良種田獵馬,供貴族玩耍享樂。在清朝全盛時期的康雍乾時代,皇帝們對于木蘭秋彌情有獨鐘。不僅將此事作為國家選拔武官人才以及考核族內勇士的大賽場,更是利用其靠近內蒙古天然牧區的優勢,作為與蒙古諸部聯絡的一種外交典禮。
當時中國還處于冷兵器時代,傳統的戰馬、弓弩等仍舊是境內作戰最為管用的武器和戰略物資。在蒙古準噶爾部以及沙皇俄國的屢次作亂中,清軍對于戰馬的需求仍舊十分巨大。因此,在河套地區再度開辟牧場,至關重要。經乾隆皇帝批準,在青海西寧等地設置了四處馬場,用于馴養、挑選良種馬,以備軍用。直至嘉慶年間,河西牧場的種馬養殖,已漸成規模。然而,隨著軍馬的供應日益充足,曾經“女真滿萬不可敵”的八旗精銳卻早已消磨掉往日的銳氣,變得貪生怕死起來。
曾經威震世界的蒙古騎兵,作為替代的軍事力量進入了滿清皇帝的視野。而這些蒙古騎兵,終將在封建時代的尾聲,像流星般匆匆劃過,無聲消失。鴉片戰爭的爆發,標志著影響中國數千年歷史的騎射被時代淘汰了。在內憂外患之中,中國封建時代最后一支戰斗力頑強的滿蒙騎兵,在名將僧格林沁的統帥下,奔赴戰場。
就像他們的祖先那樣,這支騎兵一鼓作氣,奮勇向前,重現舊日滿蒙騎射之精髓。





















